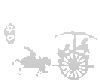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深夜底泪
生波停了掀簸;
深夜啊!——
沉默的寒潭!
澈虚的古镜!行人啊!
回转头来,
照照你的颜容罢!
啊!这般憔悴……轻柔的泪,
温热的泪,
洗得净这仆仆的征尘?
无端地一滴滴流到唇边,
想是要你尝尝他的滋味;
这便是生活底滋味!枕儿啊!
紧紧地贴着!
请你也尝尝他的滋味。
哎!若不是你,
这腐烂的骷髅,
往那里靠啊!更鼓啊!
一声声这般急切;
便是生活底战鼓罢?
唉!擂断了心弦,
搅乱了生波……战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个究竟?啊!宇宙底生命之酒,
都将酌进上帝底金樽。
不幸的浮沤!
怎地偏酌漏了你呢?
夜是属于思想者的,白日里行为方正,不苟言笑的闻一多每每都是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思潮起伏,“夜之思”是闻一多诗歌中相当引人注目的品种。
明晃晃的白日是肉的舞台,暗幽幽的夜晚则是灵的镜像,白日里的“生波掀簸”让人应接不暇,哪里有机会来舔拭自己受伤的灵魂呢?一句“深夜啊!”引出了无尽的感叹。那些不得不应付的人,那些不得不说的话,那些不得不做的事,还有,那样的转瞬即逝的快乐,那样盘缠不散的悲哀,如今皆通通卸去,只剩下这孤零零的灵魂,这颗无法安息的心对那空虚的静寂的空间,恍惚间,夜成了他脚下一潭黑漆漆的池水,它悄无声息地散发着微弱的寒光,给人以心惊胆颤的诱惑;一会儿,夜又幻为了一面竖立的古镜,它既明净又深邃,既拙朴又灵敏。在诗人的感觉中,“寒潭”、“古镜”俨然是某种睿智的境界,它尽可能撕开社会化的“脸面”,一直照彻到人的骨髓之中,让所有灵魂深处的创面与伤痕都暴露了出来。
“行人啊!回转头来,照照你的颜容罢!”这仿佛就是发自“寒潭”和“古镜”的呼唤,但又未尝就不是来自诗人的灵魂深处的催促呢。夜半时分的清醒,让诗人照见了自己枯槁的形容,伶仃的身影,于是,一滴酸楚的泪,轻轻滑了下来。“轻柔”和“温热”似遣词中有意造成的反差:①轻柔、温热是其形,而沉重、冰凉才是实;②人生征程上的沉重感、冰凉感无所不在,而这般的轻柔、温热不过是似有似无的一抹;③如此无足轻重的慰藉反倒可能使人联想到了真实的现实的可怕;④无论是“轻柔”还是“温热”,不过都是诗人无可奈何中的自我宽慰,英雄有泪,还需红巾的揾拭,但在这孤独的夜半,除了一颗孤独的灵魂,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诗人表示怀疑,这几滴眼泪“洗得净这仆仆的征尘?”当然不行,不仅洗不净,而且还因为它沿着风尘仆仆的脸面一路下来,反倒粘合进了许许多多的尘埃与苦汗,等滑至嘴角时,倒真是又酸又涩,俨然就是人生的真味。这样一来,这扑簌簌下降的眼泪又似乎毫无了轻柔温热的感觉,它根本不由人的意志所控制,“无端”地投向我们,不时提醒着我们“生活的滋味”。“无端”二字,生动地表现了诗人不堪承担之时的无奈。
接着,诗人找到自己忠实的伙伴:枕头,只有它默默无语,只有它永远温和,永远宁静,永远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具疲惫的头颅,容忍着他的粗鲁、污秽与软弱,诗人终于有了知音,有了契友,他伏在枕上,把“深夜底泪”尽情地倾泻。
苦闷和辛酸暂时得到了释放,诗人的心境逐渐平静了下来,“寒潭”和“古镜”般逼人的夜色退了下去,苦涩的泪也不再随意流淌。诗人那颗不愿安息的心又活跃了起来,白日里风尘扑扑,满是痛苦的人生固然让人伤痕累累,但那毕竟还是“生活”!除此之外,人别无选择,苦难让人落泪,但落泪的苦难又何尝就没有它特有的诱惑性呢?声声更鼓,实际上就是那不曾停息的白日的继续,他提示着黑夜里的人们,新的一天一分一秒地到来,“忽切”地到来。疲倦的诗人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生活底战鼓”刺激着他,给他勇气,催促他对即将来到的白天,即将来到的人生满怀希望,高扬起战斗的精神;但另一方面,昨日里那记忆犹新的失败与疲怠也紧紧地将他拖在床上,让他只能面对深邃的夜空想见自己的憔悴。两难的冲撞使他的心绪更加的烦乱不已。“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顽固的命运碰上了同样顽固的意志,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生活啊!/你可有个究竟?”诗人从疲倦、烦乱,从茫茫夜色中昂起头来,向苍天追问。
但天帝不愿回答。在这一瞬间,诗人强烈地产生出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他看来,主宰着宇宙人生的上帝显然对他漠不关心,上帝的金樽里盛满了“宇宙底生命”,但唯独对他这一片“浮沤”不理不睬。“浮沤”既是指作为他苦涩生命象征的眼泪,又可以说就是他这一弱小的为命运之风尘所污损了的个体。
上帝这一基督教文化的意象被闻一多所运用,这是很有趣的事。在“五四”运动以前,闻一多曾经批评基督教的教义荒诞不经,就学清华学校,特别是在参加了“⊥社”的活动后,虽又曾同意用宗教思想来激发人们向上奋斗、不屈不挠,但在总体上讲,他并没有从情感上接受基督教文化观念的影响,这里出现的“上帝”也是完全中国化的,闻一多化的,面对“上帝”,闻一多似不愿过分追述自我的罪孽,以求救赎。在他看来,“上帝”就是一位命运的操纵者形象,被上帝抛弃就是被命运所抛弃,他无所谓善与恶,而人也无所谓罪与罚。闻一多的“上帝观”是中国现代作家吸取基督教的影响的代表。
这首诗题为“深夜底泪”,是诗人命运的象征,它酸楚而苦涩,轻柔而沉重。诗以“泪”的意象来网结全篇,给诗歌蒙上一层凄清、迷离的泪光。(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