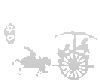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诗人
人们说我有些象一颗星儿,
无论怎样光明,只好作月儿底伴,
总不若灯烛那样有用──
还要照着世界作工,不徒是好看。人们说春风把我吹燃,是火样的薇花,
再吹一口,便变成了一堆死灰;
剩下的叶儿象铁甲,刺儿象蜂针,
谁敢抱进他的赤裸的胸怀?又有些人比我作一座遥山:
他们但愿远远望见我的颜色,
却不相信那白云深处里,
还别有一个世界──一个天国。其余的人或说这样,或许那样,
只是说得对的没有一个。
“谢谢朋友们!”我说,“不要管我了,
你们那样忙,那有心思来管我?你们在忙中觉得热闷时,
风儿吹来,你们无心地喝下了,
也不必问是谁送来的,
自然会觉得他来的正好!”
《诗人》是闻一多的自叙状、自画像,是他艺术精神、艺术追求的真切剖白,是诗的宣言。
他首先介绍了世人对“他”的评价。在世人眼里,诗人的形象怎样呢?
有人认为,诗人不过是一颗没有实际用处的“星儿”,除了“好看”,毫无现实意义,这显然是功利主义者的眼光,而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又往往在世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说,这一评价颇有代表性。
有人认为,诗人的生命脆弱、个性刁钻古怪,根本不值得亲近,这又是典型的世俗性思想意识。
终于有人对诗人表示了赞叹和欣赏,“又有些人比我作一座遥山”,诗人具有了某些“高度”,且还露出一些因“遥”而生的朦胧之美。这大概就是诗人的知音了吧?但诗人却又指出,“他们但愿远远望见我的颜色,”也就是说,世人欣赏的只是诗人那潇洒飘逸的外表,而且是远距离的漫不经心的“鉴赏”,他们丝毫也不想与诗人作心的交流,灵的沟通,因而也就绝对不可能对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深的理解和认识,对诗人那高远脱俗的理想更是一无所知了。由此可知,在任何一个世俗人的眼里,诗人都缺乏应有的价值──或者是作为物质的功用价值,或者是作为人伦的交际价值,或者是作为哲学的认识价值。世人与诗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膜。
不被人理解和认可是悲哀的,但诗人倒似乎没有这样深的悲哀,他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与那些庸庸碌碌的俗人有着层次性的差别。诗人作为精神领域中独立的探索者,自有它超越世俗认识的诸多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世俗的误会和曲解恰恰是证明了他独一无二的、难以为别人所代替的价值。于是乎,那说三道四的人们不过都是些沉溺于世俗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的营利之徒,他们整天忙碌于个人的利益,但又要不时对超乎他们理解能力的东西指指点点,这是不是有点荒唐滑稽呢?诗人讽刺说:“不要管我了,你们那样忙,那有心思来管我?”
既然如此,那么诗人与俗人、诗与现实世界之间就永远是互不相融、难以对话了么?诗人注定了只能孤立地生存在世界上,于人无用,于世无干么?显然这又并不符合闻一多的思想主张。闻一多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但那主要是为了将激情式的艺术与理智性的概念区分开来,将美的理想形态与污秽的现实区分开来;闻一多同时仍然把艺术作为“改造社会底急务。”1920年他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开头就宣称:“有艺术天能的听着!──艺术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
闻一多竭力鼓吹“艺术”的社会功效,认为“物质生活底流弊”必须用“发达的精神的生活”来调剂。调剂的方法可分“伦理”、“宗教”与“艺术”三种,三种之中,又以“艺术”最为理想,提倡艺术和美育就是“尊重人格”,就是“促进人类底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参见《恢复伦理演讲》、《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建设的美术》等文)
因而,诗人对于世俗世界有着它的不可低估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既不依靠宗教的迷狂,也不假借理性的逻辑,它属于“无用之用”,只能由世人焦渴的内在需要来摄取,又缘着人们细微的感知悄然显现。当世人与诗人在某一心理节奏上互相应合时,诗的意义就产生了。“热闷时”喝下那沁人心脾的凉风,这就是凉风的“社会功效”,也是艺术和诗的“社会功效”。
这首诗在构思上很有点“诱敌深入”的味道,全诗用意在于宣扬闻一多对诗、诗人之社会功效的认识,艺术地剖露他的“诗的宣言”。但却没有开门见山道出他的观念,而是别出机杼地介绍了几种很有代表性的“俗见”,借以引导和清理读者的思想意识,在对“俗见”的介绍中,闻一多已经有意无意地显示了他们的粗陋和偏颇,表达了一位诗人的独特的情感世界与人生态度,最后,在一个形象性的比喻中阐发了自身的独立见识。这样,即便是原本偏颇的“俗人”,也容易接受这一艺术观念了。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