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诞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注: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收入《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再加上一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得以在中国建立并迅速发展壮大。傅斯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傅斯年对考古学的发展是全力支持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他非常爱才,但又要求很高,态度很苛。比如对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他便有一清楚的标准:“‘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物质推论时,尤当记着。把设定当作证明,把设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变作近若有关,把事实未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足以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所以,作者‘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的报告尤当如此”。(注:见《城子崖·序》,收入《傅斯年选集》。)事实证明,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田野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著作,尽管由于条件所限,印刷粗糙,但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作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为考古学的发展延纳人才,奖掖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学得以循序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学的精英人才。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可以说,傅斯年领导的这一学术研究团体,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坚。李济回忆道:“我个人认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许就中断了”。(注:李济:《创办史语所与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收入《傅斯年》,学林出版社,1991年。)1948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傅斯年所长兼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即在台大文学院创立考古人类学系,培养考古人才。教授阵容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学)和第四组(人类学)。讲授的课程有:考古人类学导论(李济)、中国古文字学(董作宾)、民族学、中国民族志(芮逸夫)、中国考古学(高去寻)、体质人类学(杨希枚)、民俗学(陈绍馨)、田野考古方法实习(石璋如)、民族调查方法实习(凌纯声)……可谓极一时之选。李济、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都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先驱者。在他们的精心教授下,台湾大学培养了一批考古人类学人才,有的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如张光直、许倬云、宋文熏、李亦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傅斯年“在短短的两年中,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并为台湾的学术研究立下了不拔的根基”。(注:李亦园:《永怀师恩—记受恩于傅斯年先生的一件往事》,收入《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这种对考古人才的吸纳与培养,与其倡导考古学的理念相辅相成;使得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不断走向成熟。最后,借用张光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人才荟聚的宝库。所长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学问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义'的原则,遍采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菁英学者,把他们收集所里,专门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学者多半是绝顶聪明,读书有成,性情淳朴、了无机心的书生。……高去寻、劳干、丁声树、张政烺、陈槃、董同和、严耕望等先生都可为代表。这批人才的储集,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注:张光直:《怀念高去寻先生》,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
刊《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页75-7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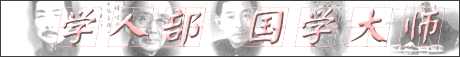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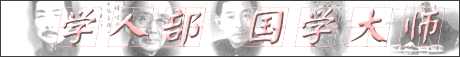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