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
中国古代先秦时代,是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时期。傅斯年看到了这种东西对峙的形势,提出“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根据《左传》、《国语》、《诗》、《史记》各书所记夏地说:“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夏在西方兴起强大的时候,东方却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说,所谓“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评考”。孔子曰:“吾欲居九夷”,也是说“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两大族类:一太皡之族,二少皞之族。太皞与太昊为一词,古经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皞氏主要有风姓,古代传说中的华胥、女娲、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属于太皞这一系统。傅斯年引证了经籍中关于太皞之记载后,归纳出两条:一、太皞族姓之国部(按:指国家或部落。傅斯年对中国古代的族姓是国家还是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从他的书名“从部落到帝国”来看,他大概认为这些古族姓还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布)于淮济间之族姓。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贡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世所贱。在周代虽居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少皞一系,据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太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已、偃、允四著姓。……种姓蕃衍……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了。”
傅斯年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录出的嬴姓所建国有:郯、莒、奄、徐、江、黄、赵、秦、梁、葛、菟裘、费。秦、赵后来成为战国时大国,秦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另有群舒、六、蓼、英氏,为偃姓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属于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区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一大片部族名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一、是启与伯益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傅斯年说伯翳(傅斯年考证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赢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二是后羿与夏争国。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争。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东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说: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他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傅斯年说: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殷、衣、韋、郼、衛、沇、兖。据他考证,这“殷、衣、韋、郼、衛、沇、兖,尽由一原,只缘古今异时,成为殊名”。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郼,殷,都读作衣。韋、郼、衛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济之间为兖州,衛也。韋、衛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纣殁后,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作奴隶,“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说:“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说中部南部)。”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亳有多处。“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认为: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作出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
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綵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淦,幼负才名,博通经史,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17岁时即被选拔为贡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没有参加朝考,也没有出仕。傅淦的父亲(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时,曾请傅淦到天津去,大约意在给他安排个官职。傅淦到天津时,可能正赶上李鸿章政务忙迫,未能即时召见。他认为李鸿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辞而去。自此靠在家乡教私塾和卖字画餬口。傅淦的妻子陈梅是江西巡抚陈阡(山东潍县人)之女,结婚时陪嫁甚丰。傅淦生活困难时,就靠变卖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3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9岁,其弟斯巌7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10岁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11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1908年的冬天,13岁的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中了进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4年,1913 年(民国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读的是古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过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所谓“兼容并包”,实际是为新派在北大挤个落脚点。当时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国学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实质是支持新反对旧。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尽弃旧学,接受新说。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的学科有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1923年由英国去德国,入柏林大学,修习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
傅斯年于1919年冬出国,1926年冬回国,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7年。从他学习的学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较宽的,而且多属自然科学,没有历史学。但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要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从罗家伦的话里理解傅斯年在欧洲求学时学得如此宽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国学问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没有材料说明他在德国学历史,但知道他读书很博,他一定也读了一些历史学的书,他的“史料即史学”思想就是从当时风行德国的兰克学派接受过来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先返乡里省亲,随后即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他担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襄助院长蔡元培先生筹划院务。院内一切制度的确立,和各种方案的制订他都贡献了不少意见,后来中央研究院的发展扩充,他有很大的功劳。”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着,傅斯年在欧洲广学自然科学且有“迷途不返”之势,到头来却为他回国后收拾旧业,为他在历史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开扩了新道路。
自此年(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陆期间,他曾兼任许多职务,其中有: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干事和总干事(1937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秋)。1946年胡适由美回国,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47年6月,赴美养病。1948年上半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年8月由美回国。冬天,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湾。1949年1月,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 日晚11时20分,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4岁。
对傅斯年的一生,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这且俟诸历史吧。我觉得胡适和他自己对他的本性和为人的评估,还是很透的。
胡适之对傅斯年可以说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对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评论,他说:“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为《傅孟真先生集》写的《序》)在这不到200字的一段话里,胡先生用了14 个“最”字来评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话,准确而又全面地描绘出一个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贵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对他自己的认识和估计。1942年12月,他于大病之后,回到李庄史语所后给胡适的信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遗憾的是,山难改,性难移。局势不静,他终难忘却国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处可以见大,更可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写有《忆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长这里不引了。
赘语
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还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恩师。1935年我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我没有去,而去日本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在社会上鬼混了几年之后,重新又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伤,活得不像个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写了傅斯年,是实事求是的,不虚伪,不夸张,有什么是什么。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对中国古代史所提出的见解,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辟见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适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学生,大多持这一相同的意见。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学问、见解也不能说已完美无缺,问题还是有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愿就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境地,对傅斯年先生的学问略提几点意见。
一、傅斯年学业可分三大段,6岁到13岁,
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晚上在家由祖父课读经籍,这是一段(1901—1908年)。14岁去天津入中学,24岁北京大学毕业,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学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阶段,在家乡他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适传播的美国的西方文化)。第三阶段,在欧洲英、德时期才真正接触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学的很杂乱。他在英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在德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虽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罗家伦)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74页。)这样说,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过来这样考虑:如果他在欧洲能以史学为主,旁及自然科学,对他后来再回过头来治史,效用是否会更大些?实际上,就他当时的主观愿望说,他是有改学自然科学就以自然科学为终生事业之心的。如他给胡适的信说:“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课一学期,现已放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注:《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华书局,1983年。)可以看出,他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是想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并非想以此为治学方法,日后对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6年治中国之学为误,国学不能为治心理学之方法,则他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不是为日后作史学、语言学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欧洲数年,他是博览群书的,文学、史学的名著也一定读了不少。 史学方面他受到史学名家一代大师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响。
我对兰克的史学,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一点是: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类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不同意说“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历史著作只在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
傅斯年的史学受兰克很大影响。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里就很有兰克的影响。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学思想。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史料学很重要,是历史学的基础;史料的整理,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些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听来好像很对,没有材料你出什么货?没有史料你写什么历史?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先秦的史料,是两千年来都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的货出来?傅先生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几篇文章,都被评为有“创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不能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货、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货,要待傅先生来出这么多新货?譬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上的这句话,古往今来也有好多人在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货,却待先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里才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货。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从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他对客观的反映,就是他从客观中取得的“理论”(意识)。这“理论”再回到他处理和客观实体的接触时,就成为他的“方法”。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人和人的接触中,人和社会的接触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傅斯年何尝没有他自己的理论。他说过“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辩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这分辩力,就是他的理论。
三、“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话也是有问题的。人世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联系确实是存在的。两种事物之间可能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和推论,不但没有危险,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就历史学家来说,陈寅恪先生就是最显著的一例。陈寅恪善于把一些看来好像全无联系的材料组织起来,发现出一些重要现象,解决些重要历史问题。陈寅恪先生的高明就在这里,他很多独到的见解都是从事物的联系上发现的。就是傅斯年先生,他的高明处也是在这里。他在文章中也是常常把中间隔着一大段的两种事实甚或多种事实,用设想或推论联系到一起而发现更多更高的认识的。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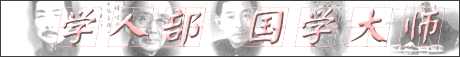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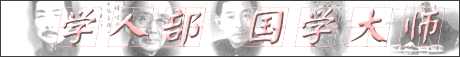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