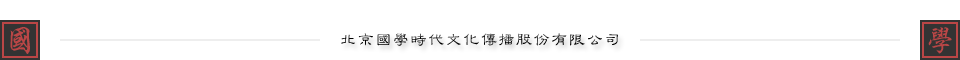乾隆后期,自施定庵、范西屏为代表的盛清国手先后下世,中国棋界后继乏人,呈现青黄不接的迹象。
乾隆、嘉庆年问,驰誉棋坛的有韩学元、李步青、顾审音、金仲柳、姜杰士等一批名手。其中韩、李曾达到程兰如、范西屏等国手让先的程度,但其余名手棋力相对稍弱。从整体的水平的下降,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时期围棋鼎盛的年代已经逐渐消逝。
从嘉庆、道光直至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国手,一般被称为“晚清国手”。其中以任惠南、董六泉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围棋衰微之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棋力比盛清国手已有大幅度的下降。
当时文士赵绍祖(1752—1833)曾撰有一篇《赠弈者任位(惠)南序》,其中有如下记载:
任君位(惠)南善于弈者也,而与余对弈,余固知其勿 及也。盖任君之弈可高余三品,虽然任君之弈未为绝技也。余先伯祖侍御星阁公好弈,弈之品与余同,尝自言与徐星友、程兰如、施襄夏、范西屏前后弈皆受六七子。然则以先伯祖之言准之余,以余准之任君之弈,而任君尚当下于徐、程、施、范三品。特以时未有徐、程、施、范者出,而以弈名者皆任君之流而任君亦遂以善弈名。
文中清晰地阐述了任位(惠)南及其同时善弈者的围棋水准,他们与盛清国手在棋力上已存有很大的差距。迄今流传有绪的多种棋谱,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乾隆后期至鸦片战争,其间超过整半个世纪,此时中国围棋为什么会节节下降?在文献不足的今日,我们不宜轻易臆断。但乾隆后期清王朝已显出由盛而衰的征兆,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清史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乾隆、嘉庆年间中衰的原因归纳为:和坤(当时权政)之专政、官吏之贪黩、军事之废弛、财用之虚耗、弘历(乾隆)之逸侈、民乱(人民起义)之渐起等类。这些都是有大量史实为依据的。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也称:“康(熙)、雍(正)之世,库存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可见待到乾隆晚年,库存帑已被耗竭一空。国势的下降,对包括围棋在内的文化、艺术,无疑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嘉庆、道光年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棋运”与“国运”竟不谋而合地先后下降,此种状况绝非偶然。可以认为:正是清代“国运”的不断衰落,才引起围棋活动的迅速走向滑坡。
及至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抵挡不住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炮火,被迫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包括棋手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中国围棋也从此急剧地转入低潮。
有关鸦片战争时期围棋发展的状况记载较少,但通过一些可信资料,也可隐约看出当时中国围棋是怎样地一泻千里。
周小松在《餐菊斋棋评》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前辈国手董六泉情况的记载:
同时对手,(董)六泉先生齿最长。道光丙午(1846年)由扬(州)客甘肃,余(周小松)与分手,后遂不复相见。
闻其投谒定制军,几至不遇。幸晋见后,定公念旧甚笃,资送颇丰。然归不数年,清贫如故,易箦之日,四壁萧然……
这段文字如实记下了一代国手的悲凉晚景,引人注目。“制军”是对总督的尊称,当时陕甘总督布彦泰曾封“定西将军”,或即其人。
董六泉与周小松“分手”时间(1846年)距鸦片战争后仅六七年。此时,董六泉被誉为国手已不下30年,在棋界负有盛誉。而“分手”的地点,又是自清初以来棋风极盛的扬州。显然,董六泉如能在扬州安身立命,是不必千里迢迢去投奔“几至不遇”的陕甘总督的。由此不难想见,鸦片战争后的棋手(即使是国手)生活已窘困到了怎样的地步。
其次,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也可窥见此时扬州棋界的没落。
从清初以来,扬州一带是海内高手云集的中心,据《弈墨•王燮序》等记载,如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众多国手,无不在扬州长期切磋棋艺,传诵一时的名句“香生玉局,花边围国手之棋”(见李麓《谷雨放船吟》),正是盛清时期国手们在扬州对垒的如实写照。但待到乾隆后期,知名国手已渐渐凋零。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即称当时扬州籍国手“仅韩学元一人而已”(李斗的记载或许不够全面,但国手数量的锐减,则是显,易见的)。至鸦片战争前后,竞连著名国手在此也不易谋生,足见这座曾被赞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寄广陵(扬州),盖如百工之居肆焉”(引自《孔尚任诗文集》的淮左名都,此时棋界状况已大非昔比。
董六泉的命运,代表着这一时期多数棋手的共同命运。而扬州地区围棋的由盛转衰,实际上正是封建时期中国围棋由盛转衰的缩影。
封建时代的棋手,对社会经济的荣枯盛衰有着独特的敏感。市场的萧条,人民的贫困,通都大邑为支持围棋活动而“争具采币”现象的锐减,等等,这一切与中国棋手的切身利益无疑息息相关。地位的低下与收入的微薄,迫使他们如不另谋职业,就只能终生为衣食劳碌奔走,根本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棋艺进修。宣统年间李子干在《争谈随录》中称:“近年以来,流风(提倡围棋的风气)顿歇或者世运(指社会动荡)益繁,人口谋生之不遑,遂无暇于艺(围棋)事。”也指出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围棋每况愈下的社会原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逐渐上升为全国最大的商埠,它的繁荣程度超过了扬州、苏州、杭州等江、浙名城,而当时棋手也唯有进入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才可能广泛接触各层次的棋界支持者。于是中国国棋活动的中心也渐渐向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型城市转移。当然,这种人地方面的变迁,远不足以改变中国围棋江河日下的总趋势。
清代末年,当中国围棋节节下降的时候,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围棋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中、日围棋的一衰一盛,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围棋自我国传人日本后,长期以来深受日本人民喜爱。早在距今400年前,日本已完成了废除围棋“座子”的重大改革。待到16世纪,日本丰臣秀吉(1536—1598)、德川家康(1542—1616)相继执政,对优秀棋家赐于世袭俸禄,使他们有条件心无旁骛地钻研棋艺,开创流派,传子授徒。从此,日本围棋在多组织、多流派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不断提高发展。到了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秀甫、秀荣、秀哉先后执棋界牛耳。“方圆社”、“本因坊”两大围棋门阀英才辈出,日本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中国。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日本人民酷爱国棋的情况也并非全然无知。在清末以前,两国围棋爱好者已进行过多次接触,从中国《杜阳杂编》、《旧唐书》到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等多种古典文献中,都散出有关于双方围棋交往的轶事。明代李言恭、郝杰在《日本考》中,甚至还扼要介绍了部分日本围棋术语,足可证明此时中国学者对日本围棋已作过并非泛泛的观察。及至晚清时期,少量日本、琉球棋谱已经输入我国,当时棋谱编印家认为“中山(指琉球)、日本,皆我同文”(见《寄青霞馆弈选•凡例》),加以收藏、翻印。但此时处于自足状态的中国棋手对海外来谱早有先入之见,并不认为其中有可资借鉴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如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幕府时期的锁国政策)、地理的、民族的(如习俗、语言等)各种原因,两国棋手彼此之间始终缺乏应有的了解,棋手的交流也迟迟未能实现。。
光绪年间,学者黄遵宪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已提到:“(日本)围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风雅士夫,无不习之者……”接着,到了光绪后期,旅日华人中也出现了以棋会友的围棋爱好者,民间的围棋交往渐渐频繁。可是,上述这些交流,或没有留下实战纪录,或仅属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相互切磋,不能用以判定两国围棋水平的高下。而真正两国棋手等级的较量,始于高部道平来访。
高部道平(1882—1951)生于日本东京,17岁入日本“方圆社”深造,曾先后师事名手岩崎健造与日本本因坊秀荣,22岁获四段称号。27岁时,他参加日本围棋组织“围棋同志会”。接着,他开始了足以辉煌弈史的漫游,走向朝鲜、中国……
1909年间,高部道平来到保定,顺路走访了在中国担任翻译的中岛比多吉。中岛是一名业余棋手,他认识当时在保定任陆军学堂总办的段祺瑞,并经常与聚集在段祺瑞周围的中国棋手交流,双方互有胜负。经中岛出面介绍,高部战胜了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所有中国名手。将对手纷纷降至让子,显示出日本职业棋手的先进技术与扎实功力。从此,高部成为段府的上宾。据日本濑越宪作《支那之棋界》引中岛比多吉的口述,当高部向段祺瑞缕述日本棋界状况,表明自己仅是一名“四段”棋手时,使在座中方棋手大为震惊。
同年,段祺瑞改任第六镇统制,他将高部道平介绍给任商部右侍郎的棋友杨士琦(见日本渡边英夫《中国古棋经之话》)。据汪云峰评辑的《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09至1910年间,杨士琦出使江南,召集南方名手在南京与高部道平对局。结果王彦卿、陈子俊等知名棋手均被高部让2子,双方互有胜负。棋界人士认为,高部的棋力不弱于已故国手周小松。于是,高部的棋名在中国不胫而走。
1910年下半年,南京举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招徕各大商埠的来往游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名手也相继来到南京。此时,多数棋手对高部的棋艺仅属耳闻,并未一试,难免将信将疑。于是,有社会名流愿出面为东道主,邀请高部至南京赴会。
南京会战,自然引起四方名手与社会人士的一致关注。上海名手范楚卿等率先登场与高部下对子,结果大败;继而被高部让2子,又败。镇江籍名手丁学博此时年事已高,被推为棋界耆宿,与高部受2子连弈2局,胜负各一(见《棋国阳秋》)。
10月,高部道平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中国名手张乐山2子对局,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这局棋谱纪录至今犹存,成为中日围棋交流史中值得回顾的一局(见《中国古棋经之话》)。接着,高部在“南洋劝业会”让张乐山2子继续对局,两人前后共弈七八十局,张乐山仅胜13局(见高部道平《围棋圣典•绪言》)。面对铁一般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双方实力悬殊。一名日本四段棋手,已足以让中国一流高手纷纷甘拜下风。那么,中日两国围棋的巨大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部道平30岁时曾归国半年,晋升五段。随后又来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保定、青岛、济南、南京、东北等地,来往中国南北前后达17年之久,到处宣传日本棋法。他与中国棋手对局数量极多。据1926年《新闻报•快活林》记载,高部让潘朗东、吴祥麟、顾水如2~3子均不下百局。又从流传棋谱中可见:他与汪云峰、伊耀卿、段俊良、范楚卿、姜鸣皋等亦曾大量对局;此外,受到他指导的还有王子晏、陶审安、何星叔、刘玉堂、林新猛、朱叔庄、周美权、唐善初、王幼宸等。高部道平交流广泛,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张静江都曾邀他对局。至于段祺瑞与张静江之弟张澹如是当时棋界重要支持者,他们与高部对局的数量更是多得难以统计。这些对局谱,部分散见于报刊围棋栏,部分被棋谱《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17年北京宣元阁版)、《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版)及《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未刊)收录,估计失散或未经发表的尚有十之七八。
高部道平除了与中国棋手交流外,还曾与同时来访日本棋家进行示范表演。如1919年lO月(阴历),高部在上海东亚饭店与访华日本棋手广濑平治郎表演;接着,他又与日本少年棋手岩本薰表演。据《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批语:这两局棋由中方社会名流集资,每局悬赏100银元。由此推断,当时对来访日本棋手待遇丰厚,这是他们乐意继高部以后接踵来访的重要原因。
高部道平的来访,揭开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的序幕。大量对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中日双方棋力悬殊的实况大白于天下,使中国棋手懂得了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此,日本围棋书刊不断引进,学习日本棋法蔚为风气,促成了中国围棋(包括废除“座子”及“还棋头”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颇有生气的变化都是在高部来访后迅速引起的,因此棋界有识之士对高部访华给予很高评价。
高部道平的来访,震动了中国棋坛,对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也引起人们的忧虑、反思。改变中国围棋的落后状况,此时已刻不容缓。
另外,通过枰场竞技,迫使中国棋手不得不怀疑传统着法是否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现代。宣统年间,李子干在《咏棋十绝》中就曾写下:“古法拘泥计本疏,兵情顷刻不相如。赵家十万长平骨,误在将军读父书!”这正是目睹中日棋手对垒后深有感触的痛切之作。名手张乐山的棋友黄铭功更是大胆地提出:“棋法自范西屏而精,亦自范西屏而始坏。”认为后来棋家唯有“大抉其藩篱”,才能使中国围棋飞跃到崭新的高度。中国棋手在迭遭惨败之后,能领悟长期奉为经典著作的“古法”也有不足法的地方,甚至敢于对“棋圣”之艺作出新的估价,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中国古谱着法既然不行于时,那末,引进日本先进围棋技术,学习日本棋理棋法,才是此时提高中国围棋水平的唯一捷径。“礼失若援求野例,未妨俎豆本因坊。”(见黄俊《弈人传·刘叔通诗》)正反映了中国棋手迫切希望掌握日本棋艺技术的心理。但是,长期以来,中、日围棋着法、规则不尽相同,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关于“座子”问题。
“座子”,指中国古代围棋在开始对局之前,规定要先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固定放置黑白各两个子,它又称“势子”、“角子”或“雅”。其中“雅”字起源甚古,音义与“岳(嶽)”同,表示中国古代曾经附会地将棋盘象征大地的传统观念。大地上的“岳”不可动摇,棋盘上的“座子”自然也固定不移。这一规定,流行中国前后至少不下2000年。而在日本,约16世纪永禄年间(1558—1569),“座子”已废除不用。清人黄遵宪《日本国志》在记述日本棋事时称:“惟行棋而不行雅”,就注意到日本与中国在围棋对局时的主要不同。
中国围棋在“座子”流行的漫长岁月里,无疑创造过许多足以传世的佳局。可见,随着围棋艺术的不断发展,“座子”的设置却使围棋的边角变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响了围棋战略战术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棋手掌握日本围棋技术。《棋国阳秋》称:“日人对弈,不置角(座)子,即其破陈式之道。华人与之对局,古谱公式,废然无所用之。”正说明此时废除“座子”已势在必行。
当然,要让“座子”从此淘汰,还须经过一个择优而存的比较过程。即先从与日本棋手交流过的中国名手之间试行,然后在棋界逐步扩大影响,最后通行于国内。
从现在棋谱资料分析,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我国名手已开始废除“座子”的探索性对局。如宣统年间李子干编印的棋谱《手谈随录》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对局130余谱,其中就有陈子俊与丁礼(理)民废除“座子”分先两局。在全书中,这两局所占比重虽小,但已说明此时“座子”的权威已被动摇。(丁、陈都是最早与高部道平交流的中国棋手,由他们率先进行尝试,是合乎情理的。)遗憾的是,这两局棋虽有可能是现存我国棋手最早废除“座子”的实战谱,付印时间也最早,但没有注明对局的准确日期。
舍此之外,在吴祥麟、黄瀛仙合编的《周小松受子谱》中,刊有张乐山与吴祥麟在上海对弈10局,均由吴先走。在这10局中,采用每两局中一局置有“座子”,一局废止“座子”的对局形式。据记载:张乐山1910年10月在南京迎战日本高部道平,然后前来上海与吴祥麟对局,1912年病殁。因此。这10局无疑弈于1910年底至1912年间。时间更准确的还有陈子俊、吴祥麟对子6局,亦载于《周小松受子谱》,其中4局废除“座子”,2局列有“座子”。据吴祥麟记载,这6局弈于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间大型城市的中国名手已在比较中、日两种不同对局形式的优劣。约经五六年后,废除“座子”的对局已占有绝对优势,终于通行于棋界。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国初期。
随着传统“座子”的淘汰,不久,关于“还棋头”的规定也逐渐废止,让子棋应还子数也起了变化。但这类规则上的变动与“座子”的存在与否相比,就只能算是细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