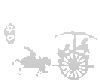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八教授颂
新中国的
学者,
文人,
思想家,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
为你们的固执,
为你们的愚昧,
为你们的Snobbery,
为你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遗产的
丰功伟烈,
请接受我这只海贝,
听!
这里
通过辽远的未来的历史长廊,
大海的波涛在赞美你。
(一)政治学家
伊尹
吕尚
管仲
诸葛亮
“这些”,你摇摇头说,
“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
你的目光继续在灰尘中搜索,
你发现了“高士传”:
那边,
在辽远的那边,
汾河北岸,
藐姑射之山中,
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
忽而又漂浮在商山的白云里了,
回头却变作一颗客星,
给洛阳的钦天监吃了一惊,
(赶尽是光武帝的大腿一夜给人压麻了)
于是一阵笑声,
又隐入七里濑的花丛里去了……
于是你笑了。
这些独往独来的精神,
我知道,
是你最心爱的,
虽然你心里也有点忧虑……
于是你为你自己身上的
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
然而你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你惋惜当今有唐太宗,
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徵;
你明知没有明太祖,
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孺;
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
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
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
你和他——你的对手,
是谁也少不了谁,
虽则——
不,
正因为
在剧情中,
你们是势不两立的——
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正如他为爱他自己
而深爱着你,
你也爱着对手,
为了你真爱你自己。
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啊!
你带满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
甩着文明杖,
来到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
你走过的地方,
是一阵阴风;
你的口才——
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
是你的零用钱,
你的零用钱愈花愈有,
你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幽灵啊!
今天公园门口
挂上了“游人止步”的牌子,
(它是几时改作私园的!)
现在
你的零用钱,
即使能兑现,
也没地方用了。请回吧!
可敬爱的幽灵!
你自有你的安乐乡,
在藐姑射的烟雾中,
在商山的白云中,
在七里濑的水声中,
回去吧,
这也不算败兴而返!
《八教授颂》于1948年6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九大学出版的诗联丛刊《牢狱篇》上发表过一部分,分别以《教授颂》和《政治学家》为题,全诗没有写完。它写于1944年7月1日,是闻一多先生发表《奇迹》后“整十五年没有写诗”,因感时“思想发酵了”而“爆裂”出来的一首讽刺诗(闻一多《与张奚若的一封信》),也是闻一多先生最后的诗作。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亦是即将取得胜利的一年。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一方面用特务、军警以威胁、盯梢、暗杀等血腥手段,阻挠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官僚政客、反动教授进行破坏。斗争前期,官僚政客、反动教授是站在前面破坏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闻一多先生针锋相对地写了这首讽刺诗,以诗的形式反映了这场斗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教授颂》、《政治学家》完全是崭新的诗篇,是闻一多先生诗歌创作的新发展。1944年,闻一多发表《儒·道·土匪》一文,大声疾呼:“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这是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后得出的精辟结论。这场大病思想上的根源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毒害有关的。而在当时,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亲自出马鼓吹儒家思想,加强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学者的愤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具有旧士大夫意识的知识分子,争谈孔学,开倒车,麻痹人们的斗志,使他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因循苟且而挺不起腰杆。在这种情况下,闻一多先生运用诗的武器,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惯于开历史倒车的中国士大夫。《教授颂》讽刺了正统学者、文人、思想家——“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的“固执”、“愚昧”、“Snobbery(势利)”,陶醉在“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遗产的丰功伟烈”。《政治学家》讽刺政客们自命清高,“伊尹吕尚管仲诸葛亮,”都只“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他们欣赏的和心爱的是“高士传”:即“在辽远的那边,汾河北岸,藐姑射之山中,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尽管“心里也有点忧虑……”,为自己身上的“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然而“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政客们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中对自己的对手愈显出“深深的爱意”,究其根源还在于爱自己、爱权力。“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因为“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所以,闻一多先生讥讽道:“具有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是“带满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甩着文明杖,来到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恰如在历史灰尘里钻营的鬼魅,凡“你走过的地方,是一阵阴风”。在自己营造的那么一个阴风惨惨的氛围里,“发散霉味儿”的“幽灵”展示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口才——“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是他们“愈花愈有”的“零用钱”。他们可以侈谈一切,理想社会、国家和未来。但他们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一切皆是空谈,开几张空头支票是无济于事的。由是闻一多先生尖锐地指出:“现在你的零用钱,即便能兑现,也没有地方用了。”还是“请回吧!可敬爱的幽灵!”那“藐姑射的烟雾中”,那“高山的白云中”,那“七里濑的水声中”,“自有你的安乐乡”。回到那虚无缥渺的仙界,回到那历史的灰尘里去,别再于此蛊惑人心,替反动统治者呐喊效命。于是基于此,闻一多先生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而目今,“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不能再侈谈“温柔敦厚”的诗教、“仁者爱人”的理想,“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闻一多先生希望“还要加强他的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三盘鼓序》)。人们是该猛醒、该自觉地起来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时代的鼓手》)
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伊丽莎白·朱曾经说过:“政治是讽刺诗的天然题材,因为贪污腐败、谋求私利和一个阶层的利益在政治中屡见不鲜”。闻一多先生此首《八教授颂》正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向破坏爱国民主运动,维护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正统学者、官僚政客进行的辛辣的讽刺,是以诗的形式发出的战斗的鼓声。张奚若先生在纪念闻一多死难二周年时说:“我很可惜你那篇《八教授颂》长诗没有写完,不然,虽然不敢说一定会‘与别人有益’,但总可增加青年人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革命运动进一步的了解。”并说此诗是一首“可与《八哀诗》媲美的大作。”此诗反映出诗人政治思想上和诗风上的转变。它的责备和讽刺流露出一个革命者的变革激情。蒲柏曾就诗歌讽刺的重要性写道:“哦!神圣的武器,留下来保卫真理吧,愚行、罪孽和横蛮的唯一的克星”。闻一多先生不仅仅是用这样“神圣的武器”来进行战斗的,而且亲自投入斗争的实践,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革命的讲演,保卫真理、捍卫真理以至流血牺牲。所以,这两首诗的形式,也与闻一多先生其他的新诗很不一样,倒是很象田间。我们读了他评论田间的《时代的鼓手》,感到那“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的“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同时,也感受到他“时代需要鼓手”的呼声。而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时代的鼓手”。《八教授颂》以漫画化的笔法,刻划出统治者及帮凶的虚伪和凶恶本质,正是一阵阵擂响的战鼓,尽管闻一多在此时,主要精力已经不放在新诗上了。经过十多年刻苦钻研祖国文化遗产,他说:“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他最终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早年他曾说过:“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论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闻一多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也正是他的壮烈牺牲。他是为了自由,为了民主而献身的,是死得其所的。况且,他曾称颂过屈原的死,“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得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事实亦证明了,闻一多的死,使中国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人民的反抗情绪完全“爆炸”开来,屈原和闻一多,都是人民的诗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