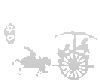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渔阳曲
白日底光芒照射着朱梦,
丹墀上默跪着双双的桐影。
宴饮的宾客坐满了西厢,
高堂上虎踞着他们的主人,
高堂上虎踞着威严的主人。
叮东,叮东,
沉默弥漫了堂中,
又一个鼓手,
在堂前奏弄,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钱戎玉碟——尝不遍燕脯龙肝,
鸬鹚勺子泻着美酒如泉,
杯盘的交响闹成铿锵一片,
笑容堆皱在主人底满脸——
啊,笑容堆皱了主人底满脸。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它清如鹤泪,
它细似吟蛩;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你看这鼓手他不像是凡夫,
他儒冠儒服,定然腹有诗书;
他宜平调度着更幽雅的音乐,
粗笨的鼓棰不是他的工具;
这双鼓棰不是这手中的工具!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寒泉注淌,
像雨打梧桐;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你看他敲着灵鼍鼓,两眼朝天,
你看他在庭前绕着一道长弧线,
然后徐徐地步上了阶梯,
一步一声鼓,越打越酣然——
啊,声声的垒鼓,越打越酣然。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陡然成急切,
忽又变成沉雄;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坎坎的鼓声震动了屋宇,
他走上了高堂,便张目四顾,
他看见满堂缩瑟的猪羊,
当中是一只磨牙的老虎。
他偏要撩一撩这只老虎。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这不是颂德,
也不是歌功;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他大步地跨向主人底席旁,
却被一个班吏匆忙地阻挡;
“无礼的奴才!”这班吏吼道,
“你怎么不穿上号衣,就往前瞎闯?
你没有穿号衣,就往这儿瞎闯?”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一—一
分明是咒诅,
显然是嘲弄;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他领过了号衣,靠近栏杆,
次第的脱了皂帽,解了青衫,
忽地满堂的目珠都不敢直视,
仿佛看见猛烈的光芒一般,
仿佛他身上射出金光一般。
叮东,叮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他赤身露体,
他声色不动;
这鼓手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真个与众不同!
真个与众不同!
满堂是恐怖,满堂是惊讶,
满堂寂寞——日影在石栏杆下;
飞起了翩翩一只穿花蝶,
洒落了疏疏几点木犀花,
庭中洒下了几点木犀花。
叮东,叮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莫不是酒醉?
莫不是癫疯?
这鼓手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定当与众不同!
定当与众不同!苍黄的号褂露出一支赤臂,
头颅上高架着一顶银盔——
他如今换上了全副装束,
如今他才是一个知礼的奴才,
如今他才是一个知礼的奴才。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狂涛打岸,
像霹雳腾空;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他在主人的席前左右徘徊,
鼓声愈渐激昂,越加慷慨;
主人停了玉杯,住了象箸,
主人的面色早已变作死灰,
啊,主人的面色为何变作死灰?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擂得你胆寒,
挝得你发耸;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猖狂的鼓声在庭中嘶吼,
主人的羞恼哽塞咽喉,
主人将唤起威风,呕出怒火,
谁知又一阵鼓声扑上心头,
把他的怒火扑灭在心头。
叮东,叮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鱼龙走峡,
像兵甲交锋;
这鼓声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堂下的鼓声忽地笑个不止,
堂上的主人只是坐着发痴;
洋洋的笑声洒落在四筵,
鼓声笑破了奸雄的胆子——
鼓声又笑破了主人的胆子。
叮东,叮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席上的主人,
一动也不动;
这鼓手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定当与众不同!
定当与众不同!白日的残辉绕过了雕楹,
丹墀上没有了双双的桐影。
无聊的宾客坐满了两厢,
高堂上呆坐着他们的主人,
高堂上坐着丧气的主人。
叮东,叮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惩斥了国贼,
庭辱了枭雄;
这鼓手与众不同。
叮东,叮东,
真个与众不同!
真个与众不同!原载1925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
《渔阳曲》是闻一多诗歌中叙事性最强的长诗。在中国民间曲艺中,“渔阳掺挝”(或称“渔阳掺”)是一种鼓曲的名称,以其愤怒激昂的格调闻名。弥衡击鼓骂曹是我国小说、戏曲中的传统题材,闻一多的这首诗就根据这一题材改编而成。
故事并不复杂:在一个高朋满座的宴会上,威严的主人吩咐一拨鼓手击鼓助兴,一位“儒冠儒服”的鼓手徐步走上阶梯献艺,他技艺娴熟,鼓声与众不同,时而如狂涛拍岸,时而象霹雳腾空,慷慨激昂,充满阳刚正气。堂上的主人是不可一世的权奸,从这鼓声中他分明悟出了鼓手的愤懑和挑战,于是面如死灰,想要发作。但是另一阵难以抵挡的鼓声如潮似浪地卷过来,把他的恼羞成怒击得粉碎,这个时候,鼓声又一换而成轻快活泼,仿佛是胜利者无所畏惧的开怀大笑,堂上的主人“一动也不动”,英勇机智的鼓手完成了惩斥国贼的使命。
虽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不无曲折,但是所有这些戏剧性的曲折都不是外在的、行动上的,“白日底光芒照射着朱梦”的时候,堂上高朋满座,堂下鼓声阵阵,末了“白日的残辉绕过了雕楹”,堂上依然是高朋满座,堂下依然是鼓声阵阵,所有的变化都是心理上的、细微的,不加仔细的辨析,几乎难以察觉。在这里,“鼓声”成了诗的中心,它是传达这一细微变化的关键,鼓手通过鼓声来怒斥权奸、庭辱枭雄,“高堂上虎踞着”的威严的主人也因为领悟了鼓声的含义而面如死灰,呆若木鸡,勿留过多的言语,也勿需啰嗦的解释,一切都尽在旋律之中,尽在这无字的乐曲之中。这样一来,鼓曲的意义几乎被诗人所神话了,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神奇的夸张吧,诗歌倒因此而颇有一层迷蒙的传奇式的色彩。
这首诗主要的功夫也就用在了对“鼓声”的渲染上。诗人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从不同角度铺垫、烘托、映衬着鼓声独特的艺术魅力。
必须指出的是,要表现这一无字的乐曲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便是因为它的“无字”,所有的思想感情都全凭我们敏锐的感觉能力去接受、去感悟,对于乐曲,感受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要“翻译”成语言符号,传递给我们读者,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第二是因为它毕竟又是比较单纯的鼓曲,较之琵琶、胡琴之类,它显然相对的变化较小,其意义似更难捉摸,也更难表达。在诗中,关于鼓声的描绘从头到尾也只有两个字“叮东”,但”叮东”之中,却又的确大有深意,这就必须依靠乐曲之外的其他艺术力量了。
归纳起来,这些艺术力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鼓手的表演方式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呈现。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的静态:“你看这鼓手他不象凡夫,/他儒冠儒服,定然腹有诗书;/他宜乎调度着更幽雅的音乐,/粗笨的鼓棰不是他的工具,/这双鼓棰不是这手中的工具”,鼓手的儒雅更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他有能力传达出更“幽雅”、更意味深长的曲调。这就暗暗地培育了读者强烈的“期待意识”,我们先天地认定在他的鼓声中确有“与众不同”的深意;接着,诗人又要言不烦地勾画了他“走上高堂”时的感觉:“他看见满堂缩瑟的猪羊,/当中是一只磨牙的老虎。/他偏要撩一撩这只老虎。”鼓手与众不同的感受已经表现出了他鼓曲的思想追求,“这不是颂德,/也不是歌功”,而是向强权勇敢地发起挑战。不久,鼓手又肆无忌惮地当堂解衣宽带,以自己的赤身露体嘲弄权贵们虚伪的道德礼仪,以致“满堂的目珠都不敢直视”。这里虽然还没有正式演奏,但鼓手的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已经在诗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等到鼓手真正的登上高堂演出的时候,诗人又写道:“他在主人的席前左右徘徊”,“猖狂的鼓声在庭中嘶吼”。这哪里是在击鼓助兴呢,分明就是用鼓声作刀、作剑,围绕在国贼、枭雄在周围向他发动起迅猛的攻击和刺杀。“击鼓骂曹”在此达到了全诗的高潮。
第二是特别注意表现听众,特别是主人”的反映。随着鼓手个性的日益施展,演奏目的是达到了,你看,厅堂里的听众,特别是那位不可一世的“主人”表情千变万化。这些变化又正是鼓手演出效果的最好的测试剂。先是一位平庸的鼓手在演出,“沉默弥漫了堂中”,宾客毫无反映,接着我们勇敢的鼓手开始了表演,但也并没有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堂上依旧是觥筹交错,“铿锵一片”。不久那酣畅淋漓、与众不同的鼓声终于“震动了屋宇”,等到他赤体而鼓时,所有的人都被震呆了:“满堂是恐怖,满堂是惊讶”,但蠢笨的客人又哪能揣测得出“主人”的怯弱,哪能品味得出鼓中的“三昧”呢?他们只是颇觉不解:“莫不是酒醉?/莫不是癫疯?”身为奸雄的“主人”毕竟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他已经领悟了鼓手的用意,“主人停了玉杯,住了象箸,/主人的面色早已变作死灰”,他想要发作,但却颓然地失败了──在与鼓声的精神较量中,他显然被击中了要害!如果说,“主人”的恼怒是鼓手大胆的挑战行为的实现,那么“主人”最后垂头丧气的失败却是他智慧过人、技艺精湛的胜利。战胜一头凶恶的野兽要比戮击它的痛处,挑逗起它的愤怒困难多了,令人欣喜的是,这两个方面鼓手都有条不紊地实现了。
第三是通过语言来摸拟鼓点的节奏和曲调,这就是全诗的基本句子:“叮东,叮东,”还有“听,你可听得懂?”“不同,与众不同”,“真个与众不同”,“定当与众不同”等等。这些句子一般是成对出现,又在全诗中不断反复,仿佛就是那鼓点演奏的声音,它们每出现一次或反复一次,鼓手的演奏就向前推进了一步,差别表示着曲调的变化;而整体上的一致性又为全诗烘托出了一种特殊的“渔阳鼓曲”氛围。
“渔阳鼓曲”本身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闻一多有意识地选择这一民间题材进行叙事诗创作,也显示了他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新的探索取向。诗人不仅沿袭着民间戏曲故事的思想感情,也大胆地借鉴着民间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复沓的运用。此外,诗人有意地用语言摸拟鼓点的节奏,这就使得全诗本身成了一首可以用鼓曲来伴唱的民歌。在闻一多的全部作品中,如此大胆地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还是并不多见的。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