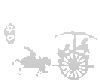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西岸
He has a lusty spring,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keats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欢!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癫!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底买卖。
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哪里去找光明来!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山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底道理?
啊!这东岸底黑暗恰是那
西岸底光明底影子。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幕;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恶雾遮不住我,”心讲道,
“见不着,那是目底过!”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绯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不是的!倒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胄,理须桡;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
鸳鸯睡了,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廉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底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绣裳下,
定有副美人底肢艳。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鹦歌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多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搭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西岸》是闻一多1920年7月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后收入《红烛·李白篇》。同《李白篇》中的其他两首长诗一样,《西岸》描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一条“宽无边,深无底”的大河把世界分隔为东西两岸,东岸弥漫着虚荣、贪婪与各种各样的痛苦;有人试图挣脱出来,把希望投向那看不见的西岸;浓雾开处,河中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小岛,仿佛就是那充满阳光与自由的西岸的缩影;就是这一瞬间的影像在东岸却引起不同的反响,少数人奔走相告,而大多数人即嗤之以鼻,即便姑且相信,也会找出各种理由否定西岸的实际意义……
这首叙事成分很重的长诗显然是寓意性的,象征性的,当你掩卷静思,就会感到它的内蕴十分丰富,颇能引发我们的诸多联想。
首先,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诗人学子生涯人生感受的写照。对于这位求学于清华学校的书生而言,西岸、东岸之类的意象又象征着什么呢?诗人有什么样的“发现”而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呢?不难想到,这一“发现”就是闻一多当时的唯美主义人生观、艺术观。长诗引为前序的诗句正出自他所崇拜的唯美主义先驱济慈之手。据现代诗人绿原解释,济慈的这两句诗大意为:“他有一个快活的春季,当明澈的鉴赏力在安适的瞬间将一切美尽收眼底。”闻一多正是希望以济慈式的“明澈的鉴赏力”将他心目中的美“尽收眼底”。富有这种览赏力的眼睛是唯美主义给他的,他立在喧嚣的混乱的此岸,希望能眺望那“美”的彼岸,尽管真实的“美”为浓雾所遮掩,世人无缘相同,但他毕竟窥见了“美”的副本。你看,河中的小岛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灿烂的鱼龙都出来晒甲胄,理须桡;/鸳鸯洗刷完了,喙子/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这与煽癫着虚荣的此岸有多么显著的差别呀!为美而歌唱,为艺术而迷醉,由此与现实的污秽、纷扰形成有意识的对立,这就是唯美主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只是,在这个利欲熏心的世界上,究竟又有多少人在真心信奉她、崇拜她、追求她呢?此岸的人们不用说没有谁会如“他”那样去河边探寻,即便是看见了也会是无动于衷的。因为真正的美对他们苟且偷生的存在是一种嘲讽、一种挑战。这就象闻一多当年在清华学校的人生:绝大多数的同窗沦于功利主义的人生追求中,或者贪图享乐,或者发奋求学,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尽快地适应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或如中国没落市民般及时行乐,或摄取各种世俗的荣耀之后更高级地及时行乐;但是,又有多少人在思考人生、在探寻人生的真理,乃至甘愿为自己美丽的理想而献身呢?沉溺于唯美主义人生理想的闻一多是孤独的,因为他所认为的人生光芒在他人看来毫无价值;但他同样也是幸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就从这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中出发了。
其次,我们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某种生存方式的揭示。或许是因为历史,或许是缘于命运,人类的生存境遇总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多少年过去了,东岸与西岸的不同就很可能是触目惊心的。如果东岸总是“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在没有真、善、美的土地上颠簸折腾,那么,历史就会孕育出自己的幻想,于是,就有人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去远方寻找希望。尽管江河横亘,尽管视线的尽头仍是水天茫茫,但反抗的骚动总是难以避免的,“啊!这东岸底黑暗恰是那西岸底光明底影子。”其实西岸究竟存不存在,是否就肯定是阳光明媚,这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里冲出樊笼的人们需要“西岸”,他们完全可以构想着属于自己的“西岸”。这时候,诸如河心小岛上的一些依稀的景观就成了他们追求的动力。成了他们改造东岸的勇气。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精神,没有他们,人类的一切进步、革命都会不复存在。但是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新生的希望,也有陈旧的桎梏。在每一次前进的初期,传统的力量往往还可能占居主导地位,从思想上、舆论上对新生的力量构成束缚、压制甚至摧毁。所以说,当东岸那位冲出樊笼的“他”向人们宣布他的发现时,志同道合的朋友几乎没有。人总是这样的具有二重性:他既向往光明、渴望革命,又害怕动荡,抱残守缺、维持现状;况且长时间地沦落于痛苦的渊薮,痛苦本身倒会变得轻盈动人起来。那么,人类的进步就没有希望了么?有的,不是还有人在发问:“为什么”吗?只是这一天的到来还需要好几代人付出更艰难的努力。
在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上,我们不妨又可以将长诗的寓意明确一点,这似乎就是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历程的艺术表现,一条长河把我们与世界分隔开来,我们这古老的东方大国(东岸)生活在封建的苦雾之中,西方世界(西岸)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道。终于有一天,不愿继续忍受封建苦雾的逆子贰臣出现了,这些“狂人”把西方文明的影象带回到家乡,于是,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阵阵波澜,有的骂他们是“数典忘祖”的疯犯,有的以维护“民族特色”相对抗(“西岸他岂是为东岸人?”),有的中西调合,以“稳”为上(“河太宽,雾正密,/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冲破阻力、无所畏惧的开拓者却为数寥寥……
我们对《西岸》作了这几种意义的分析,这是不是就把这首长诗分解得支离破碎、各不相干了呢?或者有的读者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几种意义总不都是闻一多当时的思想吧,诗人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样的担心和疑问都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按照现代阐释学的理论来讲,诗的寓意很可能就有彼此不同的多元指向,而诗人也不一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固定用意。
当然,这样的理论也绝不是用来为那些混乱的千奇百怪的阐释寻找理由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我们所分析的诸种意蕴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互生发、相互过渡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某种“有机性。”我认为,在以上几种意蕴之间,这种“有机性”是存在的。
诗人不满现实,寻找唯美主义人生理想,这固然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大有区别,他们一为单纯,一为复杂,一为具体,一为抽象;但是,个人的人生追求往往又是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的缩影,这是毫无疑问的,诗人寻找唯美主义人生,这也是人类自我改造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地说,一位敢于在具体生存环境中嫉世恨俗的人必定也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开拓者;同样地,中国传统社会面向世界,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亦属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典范,那些在“铁屋子”中呐喊反抗的“狂人”恰恰就是闻一多式的孤傲不驯之人。
诸如此类的抽象、复杂以至于有点庞杂的思想要用诗的方式表达出来,应当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许就诗的文体特征而言,就注定了长于抒情,叙事也不大可能过分宽泛,至于用诗的形式来写“寓言”,这显然会遇到不少麻烦,所以在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类似于《西岸》式的“寓言”长诗实在难得一见。青年人闻一多在中国新诗诞生发展的初期就冲破困难,大胆探索,其精神相当可贵,尽管诗歌难免有点枯燥干涩之嫌,但在艺术史上却功不可没。在艺术探索中,《西岸》本身也是一次向往“西岸”的尝试!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