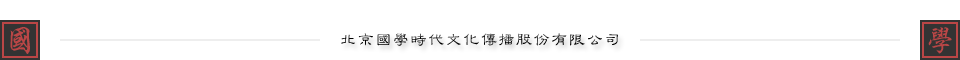康熙帝玄烨(1654—1722)是否会下围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正史中并无玄烨弈棋的记载,但是在野史、轶闻中却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例如: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段记载:
清初鳌拜辅政,因正白旗圈地事,直隶总督朱公(昌祚)、巡抚王公(登联)、户部尚书苏公(纳海)与之龃龉,乃悉加诛夷,圣祖不预知也。尝托病不朝,要亲往问疾,圣祖幸其第,入其寝,御前侍卫和公(托)见其色变,急趋至榻前,揭席刀见,圣祖笑曰:“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即返驾。以弈棋召索相国(额图)入谋。数日后,鳌拜入见,召羽林士卒立擒之。
又据周家森《留余簃弈话》载:
黄霞,字龙士,又字月天,清仪征入。善弈,能自出新意,穷极变化,康熙时称为“弈圣”。尝十万寿节日,在御前围棋,下完后于棋盘上排一“寿”字,而四角上亦均各排蝙蝙一只,以示福寿之意。殊为难能可贵矣!
以上所引两段材料,皆透露出玄烨喜爱围棋的些须情况,但是否事实,由于缺乏旁证材料,还难以断言。即以康熙除鳌拜一事看,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载:
康熙八年,上久悉螯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螯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系之。
其中并无玄烨以弈棋召索额图入谋的记载,或许《清朝野史大观》另有所据,只是我们今天难以查考而已。
关于吴三桂如何谋杀永历帝一事,某些史料语焉不详。清人笔记中的刘献廷《广阳杂记》提供了一些细节:
……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辈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予曰:“闻帝崩之日,天有风云之变,果然否?”曰:“吴三桂既得密旨,请帝于北门库饮弈,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
由此可知,吴三桂是奉清帝密旨后,请永历帝饮酒弈棋,加以谋害。据刘献廷讲,此事乃江宁吉坦然亲眼所见。坦然曾随其父扈从永历帝去云南,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后出县流寓粵东。对云南的事知之最详,故他的叙述大致是可信的。
吉坦然的叙述表明,永历帝显然喜欢饮酒弈棋,吴三桂大约知道他的这种嗜好,所以用为诱饵,将他骗来杀害。
张潮(1650—?),清文学家,字山来,号心斋,安徽歙县人。以岁贡任翰林院孔目。他所著的《幽梦影》中有一些关于围棋的妙论,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虽不善书,而笔砚不可不精;虽不业医,而验方不可不存;虽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备。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答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欵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极琴心之妙境;“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极手谈之妙境。
张潮的这些妙论,充满生活的情趣,也表现出封建文人的高雅情怀。如若将其中的围棋言论择出连接一起,就会构成一幅生动的图景:“虽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备”,“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夏雨宜弈棋”,“白昼听棋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难道不是作者围棋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张潮认为“翰墨棋酒”胜过“花月美人”,在封建文人圈子中,不见得会引起广泛拥护,但在那些胸怀磊落,志趣高雅的文人中,自会得到充分地响应。自唐、宋以来似乎已成定论。
与张潮基本同时的尤侗(1618—1704),康熙时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他写过一篇《棋赋》,其中有这样的字句:“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与张潮遥相呼应,表现对围棋的极端推崇。尤侗的观点自然有些偏颇,但也确实道出康熙年间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围棋唯一的坏处就是太迷人,烟酒可以戒,唯有围棋无法戒。一个人一旦学会下围棋,就等于找到一个不能分离的“情人”,她将伴随你快乐地度过终生,而你却无从抗拒。
乾隆时期,社会上的文士名流推崇围棋,有助于围棋浪潮的不断高涨。其中应该特别提到著名诗人袁枚,倡导围棋不遗余力。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知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县。年四十即告归,筑“随园”于江宁之小仓山,专以著述诗文为事。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七十余卷及其它著述三十余种。
袁枚一生嗜好围棋。其所著《山中行乐词》云:“何物共闲戏?围棋亦偶然。买碑争旧搨,染笔试新笺。食品何曾纂,茶经陆羽编。搜奇兼志怪,俱是小游仙。”诗中所列举的几项;围棋、金石、书画、饮食、搜奇,构成了袁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但诗中说:“何物共闲戏,围棋亦偶然。”是不是袁枚只是偶尔下下围棋呢?恐怕这样写只是想表明围棋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而据有些资料记载,情况也不尽如此。例如晚清学者俞樾曾看过袁枚玄孙袁润所保存的《袁随园纪游册》,其中所记袁枚79岁、80岁两次出游苏、杭、浙东、金陵期间,几乎天天下棋,并详细记录输赢情况。俞樾因此题诗云。“日日舟窗几局棋,输赢几子必书之。”可知袁枚对下棋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且愈老兴趣越浓。
在袁枚的诗集中,咏围棋的专篇和散句颇为不少。如《观弈》:“清簟疏帘弈一盘,窗前便是小长安。不关我事眉常皱,阅尽人心眼更宽。黑白分明全局在,输赢终竟自知难。凭君着遍飞棋好,老谱还须仔细看。”再如《咏观棋》:“悟得机关早,都缘冷眼明。代人危急处,更比局中惊。张步临奔海,陈宫见事迟。分明一着在,未肯告君知。肯舍原非弱,多争易受伤。中间有余地。何必恋边旁。”模拟观棋人的心情,颇为传神。从“肯舍原非弱,多争易受伤。中间有余地,何必恋边旁”一句看,袁枚对棋理还是很有研究的,估计他的棋也下得不错。
袁枚曾为棋圣范西屏、国手徐星标标撰写墓志铭,对他们的精湛技艺和杰出人品推崇备致。袁枚曾亲见西屏对弈,可能与西屏有较深的交往。他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后接精髹器者卢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醰粹如西屏,然后叹艺果成皆可以见道。今日之终身在道中,令人见之怫然不乐。尊官文儒,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一艺之成皆可以见道,谁都会这样说,并不算出奇的言论。而袁枚将“尊官文儒”与西屏等人对比,认为他们“终身在道中”,“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叹,透露出袁枚对现实中那些“尊官文儒”的讽剌与不满。
围棋虽然长期名列中国四大艺术之一,但在历代士人心目中,难与诗文、书画比肩,因此专事下棋的人也被看作技艺之徒。这种情况在清代已有很大改变,也就是说,围棋作为中华的国技,日益受到士人的尊崇;国手的声望也与日俱隆,到处受到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热烈欢迎。我们可以用雍、乾时期的著名诗人沈德潜、赵翼与范西屏作一比较,沈、赵的诗名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之内,难比范西屏的棋名举国震响,有口皆碑。而范西屏在全国各地受到的欢迎和款待、士夫名流皆以结识为荣,更是沈、赵所难企及的。袁枚是雍、乾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他对国手的称誉,在社会上会带来很大影响。且看他为范西屏所写的墓志铭:
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将以棋名,松风丁丁。
直是认为西屏的名望,竟比颜回、曾参这些二等圣人还要高。评价似有过甚之处,但也未必不是现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删定总目提要。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叙及围棋,对于了解乾隆、嘉庆时期朝野围棋的兴旺情况很有帮助。
纪昀本人也会下棋,但他比较欣赏苏东坡、王安石对围棋的态度,即不以胜负为怀,着重于追求其中的意趣。《阅微革堂笔记》中有“弈棋杂感”一则,抄录如下:
南人则多嗜弈,亦颇有废时失事者,从兄坦居言:丁卯乡试,见场申有二士,画号板为局,拾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对着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闲遣日,原不妨偶一为之,曰此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东坡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荆公诗曰:“战罢两奁收白黑,一抨何处有亏成?”二公皆有胜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践此言,然其言则可深思矣。帝卯冬,有以八仙对弈图求题者,画为韩湘、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而铁拐李枕一壶卢睡。余为题曰:“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今老矣,自迹生平,亦未能践斯言,盖言则易耳。
纪昀所记场中二士,为弈棋争胜,连功名都不要了,足见围棋迷人之深。这种作法自然是不足取的。纪昀由此而发的感慨也很有意思,他认为苏东坡、王安石对棋局的胜负看得很超脱,但在生活中却很难超然物外,即“皆有胜心者”。纪昀并且承认自己也达不到与世无争的地步。看来局中的胜负和人间的“胜负”是有差别的,然而人活在世上,没有一点胜负心,形同死灰槁木,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围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有强烈的胜负,符合了人的欲念和世间的竞争法则。如若没有胜负,它也很难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赢得亿万爱好者的心。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段乾隆时期高手程念伦与乩仙下棋的事,读来颇有趣:
程念伦,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间,来游京师,弈称国手,如皋冒祥珠曰:“是与我皆第二手,时无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门人吴惠叔等扶乩问仙善弈乎?判曰:“能。”问:“肯与凡人对局否?”判曰:“可。”时念伦寓余家,因使其弈。初下数子,念伦茫然不解,以为仙机莫测也,深恐败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颤,始敢应一子,意犹惴惴。稍久,似觉无他异,乃放手攻击,乩仙竟全局覆没,满室哗然。乩忽大书曰:“吾本幽魂,暂来游戏,托名张三丰耳。因粗解弈,故尔率答,不虞此君之见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长安道上,鬼亦诳人。”余戏曰:“一败即吐实,犹是常安道上钝鬼也。”
所谓“仙”,无非是扶乩的巫师装神弄鬼,他虽自誇善弈,但遇到高手,自然会全军尽墨。程念伦、冒祥珠大约是士大夫中的高手,在乾隆时期弈坛强手如云的情况下,能达到二手的程度,已是相当不错了。只是关于他们弈棋的情况,除上述一则趣闻之外,史料中却未留下丝毫记载。
围棋一般是两个人下的,人多了也可。比如“联棋”,有时竟多达几十位,分为两班人马,一人走一步,轮流走下去,取其热闹而已。
那么,一个人是否也能下围棋?答案是肯定的。不仅高手,既使一般爱好者,在研究和学习棋艺的过程中,也常常自己和自己下棋。这实际上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即在头脑中设一个假想的对手,先构思他怎么走,然后再构思自己如何应对。一盘棋就这样下出来了。清代散文家魏禧(1624——1680)所著《魏叔子集》中,有一篇《独弈先生传》,记述了一位专门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黄在龙。
据魏禧描述:黄在龙性不治生产,绝世务而好弈。常闭户居,户外人闻子声丁丁然,窥之,则两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杀。或默然上视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称曰:“独弈先生”。
“独弈先生”兄弟三人,伯好鼓琴、仲好艺花竹,而先生独好弈。或求对,亦不辞也。先生开枰布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问可否?伯、仲各以意对,先生说:“若长于守,若长于攻,然皆偏将材也,使握中权,决机两阵,难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独弈未尝稍衰云。
魏禧发表感想说:“古嗜弈者众矣,未有独弈者?曰:有之。弈,攻围冲劫,变化通于兵法。诸葛武侯卧隆中时,未闻有十夫之聚,指挥旌帜,教坐作也。出而战必胜,以仲达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独居抱膝时,日夜之所思,手所经营,未尝不在两阵间也,非独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测识哉!”
魏禧说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独自研习兵法,有类于“独弈”,是不错的。但因此认为黄在龙的独弈,其意不可测识,则未免贻笑大方。前面说过,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独弈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黄在龙既使比一般人更嗜好独弈,恐怕也难说他象诸葛孔明一样,有志图王吧。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有关围棋巨星吴清源的一段趣事。吴清源也可说是一位“独弈”的专家,他独自一人苦心研究出的新手、新定式不胜枚举。因此,日本著名九段棋手武官正树曾说:“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感到很光彩,有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自然,吴清源所创造出的新手和新定式,在未发表之前属于个人“专利”,是秘而不宣的。而一旦在实战中走出来,常常使对方措手不及。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吴清源——高川格”三番棋中,吴清源在“大雪崩”定式中走出向里曲的新变化,使高川格大惊失色。在观战室中的年轻棋手纷纷议论说:“吴先生把定式搞错了!”殊不知这正是吴清源苦心孤诣的变着。这局棋最终以吴清源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成为维持摇摇欲坠清王朝的中流坻柱。他学识渊博、诗文传世,文治武功足以名彪青史。一般的学生大约只知道曾国藩是屠杀天国义士的刽子手,稍有学识的人还知道有一部《曾文正公文集》。然而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曾国藩一生嗜棋如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围棋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旋任翰林庶吉士,时年28岁。在他传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自己日常的围棋活动。仅就这些日记中的记载大致统计,从道光二十一年起的十三年中,他共对弈一千三百余盘棋,观棋还不在其中。自然,实际对局的数目还不仅于此。
据记载,曾国藩“终身患癣,每晨起必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从记载中看,有时他一天下两盘棋、有时一天下三盘,最多一天下四盘。作为朝廷大员,曾国藩公务繁冗,但他常忙里偷闲,弈棋遣兴。有一次他在处理两百件公文后,仍要下两局棋方能入睡。有一天曾不断接待来访者五回,忽然发了棋瘾,非下两盘棋后才人内室休息。还有一次为来访者书写对联十七幅,不顾疲劳继续弈棋。有时半日内分別与两人对阵,有时一日内连与两人对垒角逐。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日记中亲手所记,可见围棋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不仅如此,往往下完棋后余兴未尽,半夜时分进了内室,他还要摆开棋盘,或打谱或复盘,仔细玩味一番。当身边无人可为对手或遇风雨无法外出,曾国藩只好自己一人对弈,实在无以遣怀,就把夫人拉出来下一局,也有自得之乐。
曾国藩的棋友,在他日记中就可找出五十余位。从身份看范围极广,诸如亲朋好友、幕僚职属、看病的大夫、过往的官员以及不第的士子,还有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弟媳等等。除此而外,当时国手周小松、黄南坡等也与曾国藩有过棋艺交往。曾国藩于棋友常引为同调,情意眷眷。棋友别去,他亲送行,棋友辞世,他则痛哭,并吟诗作赋以寄怀念之情。这里应特别提到曾国藩与僚属下棋,大凡他棋瘾发作,即不顾封建等级尊卑的界限,常找下属手谈。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小小的桐城县令薛炳炜是他常年的棋友。有一个不曾记下姓名的普通举人,因棋艺颇佳,也受到曾国藩的青睐。咸丰九年十二月,已是子夜二更时分,曾国藩旁观鲁秋航、李榕二入夜战,四时许才入睡。之后几天不下棋,技痒难耐,就悄悄到下属如毛鸿宾、胡莲舫家中求战。以总督的身份,为了下棋,不惜屈尊下就,这不正说明围棋的巨大魅力吗?
不仅在家中弈棋,既使公务在身,曾国藩也往往见棋就忍不住要比试一番。道光年间他人宫当值,至勤政殿引见前也要下两盘棋过瘾。一般官员见皇帝前往往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松懈,而他却要先下两盘棋,棋瘾之大是自不待说了。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国藩率军征战,更是以围棋随身自娱,而且愈是不顺心愈要下棋。这时围棋已成为他排遣忧患,不可须臾分离的精神寄托。咸丰九年,在三河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和爱将李续宾被太平军击毙,不久湖南宝庆被围,曾国藩“心急如焚”,遂拉棋友吴子序弈棋两局。其间他疟疾发作,手疼兼生坐板疮,可以说是坐立不安,只好下棋以“解心烦”,看完病便与大夫郭霈霖手谈两局。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正与程桓生下棋,忽接圣旨,朝廷补授其为两江总督。一时府邸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程桓生欲罢战,而他坚持棋局收盘后才接见道喜的客人。咸丰十一年,英王陈玉成一举围歼湘军三百余人,曾国藩“心烦意乱”,遂下三盘棋定神。同治二年二月在丁家洲船上,一日之内连战六局,每局约两刻许。七月金陵解围战失败,他“寸心如割”,又下两盘棋。不久其妾陈氏病重吐血而死,“哭声凄凉”,他“心绪殊劣”,又与欧阳兆熊连弈四局以解哀愁。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曾国藩由安庆赶至金陵,亲审忠王李秀成。一时找不到对手,便与其弟曾国荃随便下两局应景,据他在日记中说,只有这样才算未虚度时日。
同治四年四月,朝廷调他镇压捻军,他自南京北上,一路上因剿捻失败“焦灼之至”,途经山东泰山,上山前在泰安考棚中与人对弈两局,下山后又下两局。返宁途中在淮安适逢漕运总督吴棠,两人是多年棋友,遂弈战不休,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
以上所述是曾国藩在戎马生涯中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他不仅以围棋排忧解难,也曾有意识地将围棋用于军事。据载,一次部下向他报告大将多隆阿收队之法,他便命人“以棋子摆列阵式”进行实战研究。
曾国藩一方面嗜棋,一方面又屡屡发誓戎棋。大约爱之深反又恨之切,矛盾的心情颇为有趣。他认为下围棋“最耗心血”,多下則“头昏眼花”,有时“眼蒙太甚”,“明知旷工疲神而屡蹈之”。一度发誓“戎棋”,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为棋所困,费光阴至一时之久,妨正务,以后戒之。”甚至说再下棋便“永绝书香”,决心不谓不大。为了戎棋就只看他人下棋,结果如何呢?仍“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愈戒棋瘾愈大,终于也未能戒掉。
清代围棋的繁荣,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小说之中,著名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中都有关于围棋活动的描写。由于这几部小说均产生于康熙、乾隆时期,也就间接地反映了康、乾盛世社会围棋活动的某些情况。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是否喜爱下棋,还未见到这方面的材料。但在《聊斋志异》中谈到围棋的有十五篇之多,较为著名的有《娇娜》,《连琐》、《陆判》、《云萝公主》等。还有一篇《棋鬼》,对现实生活中嗜棋如命的人作了形象、深刻的描绘。小说写一个“湖襄人”,癖嗜弈,产荡尽。“父忧之,闭置斋中,辄逾垣出,窃引空处,与弈者狎。父闻诟詈,终不可制止。父赍恨死,阎王以书生不德,促其年寿,罚入饿鬼狱”。后来“东岳凤楼成,下牒诸府,征文人作碑记,王出之狱中,使应召自赎”。谁知这位书生又半道与人下棋,迁延误期,结果“仍付狱吏,永无生期矣”。
小说虽然写的是鬼,实际上却是刻画现实中活生生的人。请看如下描写:
扬州督同将军梁公,解组乡居,日携棋酒,游林丘间。会九日登高,与客弈,忽有一人来,逡巡局侧,耽玩不去。视之,面目寒俭,悬鹑结焉,然意志雅温,有文士风。公礼之,乃坐,亦殊搛。公指棋谓曰:“先生当必善此,何不与客对垒?”其人逊谢移时,始即局。局终而负,神情懊热,若不自己。又着又负,益愤惭,酌之以酒,亦不饮,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不逞溲溺。方以一子争路,两互喋聒……
寥寥几笔,一个嗜棋而棋力又不高的形象跃然纸上。爱丁棋的人都知道,象蒲松龄所描写的这种类型的人,俗称“屎棋”经常可以见到,不能不说蒲松龄对生活的观察十分仔细,勾勒人物也非常传神。蒲松龄写这个故事的用意比较明显,旨在讽喻嗜癖误事。但世上因嗜癖误事的例子尽多,为什么作者偏偏选中嗜棋呢?我们可以设想,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触动了作者,使他产生了“劝戒”的欲望。作者最后形容嗜棋的人说:“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也就是“见弈而忘生死”,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曰有,围棋之迷人可谓深矣。
《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围棋的地方不多,除第六十二回写“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这样几个字以外,还提到过丫环们用围棋“赶子”(一种简单的盘戏)。但是在后四十回中,有关围棋的描写却多了起来。例如第八十七回写惜春和妙玉下棋,还提到古谱中的著名套子:“倒脱靴”、“茂叶包蟹”、“黄莺搏兔”等。再如第九十二回较详细地描写贾政与清客詹光下棋的情景。上述的情况显然表明,曹雪芹与高鹗对围棋的认识和喜爱,有一定的差异。大约高鹗比曹雪芹嗜好下棋,所以在他的笔下,围棋自然而然成为描写的对象。近年海外有些学者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系出于一人手笔。但依笔者浅见,即使从书中前后对围棋的描写不同来看,出于一人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清代小说中,于围棋史最具参考价值的,要算《儒林外史》。书中有三处关于围棋的描写,对当时社会上的围棋活动作了真切而深刻的叙述。
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娄公子故里遇贫交”写王太守与蘧公子一番对话:
……当下酒过数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主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宁问:“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以“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反衬“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表现当时“清官”与”贪官”雅俗之不同,体现了作者对官场情况的反思以及深沉的精神寄托。
第五十三回“国公府雪夜留宾,来宾楼灯花惊梦”,描写南京妓院里的围棋活动。吴敬梓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取材于秦淮河畔发生的事情。秦淮河历来为六朝金粉之地,“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比较高级的妓女,为了侍奉公子王孙、达官贵人,都需要学习琴、棋、书、画,以抬高身价。“来宾楼灯花惊梦”即写妓女聘娘向国手邹泰来学棋时发生的故事。
国公府的亲戚陈木南去“来宾楼”梳栊聘娘,恰值聘娘与南京国手邹泰来学棋。陈木南乘兴取出一锭银子权作彩头,入局与邹泰来对弈,从七子至十三子,只是下不过。因说:“先生的棋实是高,还要让几个才好。”邹泰来说:“盘上再没有个摆法了,却是怎么好?”聘娘说:“我们另有个摆法,邹师父,头一着不许你动,随便拈着丢在那里就算,这叫个凭天降福。”邹泰来笑道:“这成个什么款,那有这个道理。”陈木南逼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来混丢在盘上,接着下了去。这一盘邹泰来被杀死四五块,陈木南正暗欢喜,又被他生出一个劫来,打个不清。陈木南又要输了,聘娘手里抱了乌云复雪的猫,往上一扑,那棋就乱了……
这一段故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当时围棋国手的一些生活情况。作者在这一回的开始说:“又有那一宗老邦闲,专到这些人家来替他烧香、擦炉、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书画。”邹泰来即是这样一个“老邦闲”,他虽身为国手,但为生计所迫,只好出入妓院,靠教妓女下棋,赢些嫖客的彩金混日子。从史料记载看,清代康、乾时期的国手,其最好前途即是出入达官富豪的家门,充当清客。其末流即是像邹泰来那样,在妓院充邦闲。因此,吴敬梓笔下的邹泰来,是对现实生活中棋客命运的真实写照,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然而在民间,也有一些身怀绝技的人,不甘仰承豪贵的鼻息,依仗一点小手艺自食其力过活。《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记述一个名叫王太的人,自小最喜下围棋。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他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为生。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去,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一个穿宝蓝的说:“我们这位马先生前日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他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一个穿玉色的少年说:“我们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只有这卞先生受两子还可以敌得来。只是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实费力了。”王太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说:“你这样一个人,也晓得看棋?”王太说:“我也略晓得一些。”撑着看了一会,嘻嘻的笑。那姓马的说:“你这个人会笑,难道下得过我们?”王太说:“也勉强将就。”主人说:“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马先生下棋!”姓卞的说:“他既大胆,就叫他出个丑何妨。才晓得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辞,拿起子来,就请姓马的动着。旁边的人都觉得好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觉得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盘,站起身来说:“我这棋输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晓得,姓卞的说:“论这个局面,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一些。”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屎棋的事,我杀过屎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从这一段故事里,我们可了解一些当时南方围棋活动开展的情况。像妙意庵国手棋会、马先生在扬州盐台处下棋赢两千多两银子等情节,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围棋回手的某些生活。吴敬梓笔下的马先生,是一位靠下棋吃饭的“职业”棋手,王太虽然棋艺很高,却靠卖火纸筒为生。在这里,吴敬梓实际上对王太这样自食其力的市井小民,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名列儒林而毫无逊色。但对国手马先生,笔调中则颇含讽剌的意味。
吴敬梓生于1701年(康熙四十年),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与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本人喜爱下棋,因此他笔下所描写的围棋故事,即使在细节上也绝无隔膜之处。他长期居住围棋兴盛的南京,晚年也曾到过当时的围棋中心扬州。大约他接触过一些围棋高手,并以他们的生活为原型,塑造了邹泰来、王太、马先生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王太这个人物,寄托了作者的赞美与期望。笔者认为,王太这个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虚构的理想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反映。象类似的民间棋手,在其它史料中也有所记载。例如前面己提到的,《扬州画舫录》中弈胜范西屏的“担草者”等等。我们若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太,与《扬州画舫录》中的“担草者”对照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康、乾之际,在民间确实出现了一些业余围棋高手,他们不以棋名世,而是自食其力,但是他们的棋艺却可以和当时的国手相媲美。
清代的著名小说中,还有一部《镜花缘》,描写围棋活动既多而又详细,这是因为它的作者李汝珍(约1763—1803)极为嗜好围棋。李汝珍曾编选《受子谱》二百余局,对棋艺有相当研究。在《镜花缘》中,下围棋是百花诸仙女和才女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只是这些下棋的场面写得不算精彩,其间还充斥一些围棋知识的议论,破坏了艺术的形象性。对于围棋史来说,也较少参考价值。
晚清还有一部小说《新聊斋》,仅存残本卷一,不甚著名。作者“治世之逸民”,具体姓氏不详。书中有一篇《谈棋》,有可注意之处。小说叙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凫山乡人周鹆,以围棋邀知于曾(国藩)、彭(玉麟)诸军帅,居军慕之上舍。周鹆善于谈棋,以口代手,不假枰局。尝说:“吾生平阅人多矣,凡弈者,……唯口谈至八十余着而不紊者,仅袭侯曾纪泽。”小说又通过一僧人之口介绍彭玉麟:“我闻李军请济师,彭公且至,大夫也,醉心于此道……”
曾国藩、彭玉麟、曾纪泽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关他们在军中弈棋的情况,也见于其它史料记载。例如《清代轶闻》曾记述晚清大国手周小松与曾国藩弈棋往来:
曾国藩最好弈,而不工。尝召小松弈,意厚赆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棋为九片,皆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赆。曾患癣,终身不愈。每与人弈将负,则半身伏案上,癣益痒,爬骚肤屑盈案,人莫不厌苦之。尝与某武员弈,至相诟詈,几至挥拳。明日乃嘉其有胆气,保荐之。
从这一段记述,笔者颇疑《新聊斋·谈棋》,是根据周小松的某些经历,所敷衍的一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