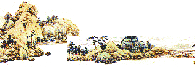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大雪纷飞,扯絮丢棉,连降数日,神佑大地白茫茫一片。山里的人大多都缩在家里依偎在炉火旁或干脆钻在被窝里不起来,以此来躲避冬日的严寒。但此时小山却顶着风雪沿着崎岖的小路艰难地向前跋涉。咕滋咕滋,盈尺的积雪在小山的脚下呻吟着。路上没有行人,小山行走在这银色的世界,尤如一只企鹅给白色的大地点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小山这次回家是公差。他很久没有回去了,很想回家看看。看看爹娘,看看二喜和范娃,当然他也想看看日夜思念的燕子。自从他离开家几乎没跟燕子见过面,不是他不想,而是没有机会。那次他回来,也没见到燕子,大脚婶跟他说燕子找个了婆家,那家答应给她家盖三间瓦房,燕子同意了。听说还跟那男的去了两次平川,说是去撕衣裳,城里的布多。燕子撕回来很多布,但一件衣裳也没做,大包小包的包着放在箱子里。燕子还是穿着原来的那些旧衣裳。也很少看到她脸上有笑容。小山听说后,心里很难过,回到厂里他就一门心思地上班,空了就借些书看。为了多挣俩钱,他还经常给别人顶班。后来县总工会办文化补习班,小山报了名。每天晚上,只要他不上班,他从来没有缺过课。有一天下大雨,县城的街道上汪起了没膝的雨水,小山披着雨衣趟着积水走了半个小时才到总工会,那天晚上来上课的只有他一人。厂长看中了小山的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把厂里办墙报的事儿交给了他。办墙报这几天是可以不上班的,但小山坚持上班和办墙报两不误,厂长对此大加赞赏。后来,中央决定从上到下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神佑县抽调了大批人员组成了庞大的落实政策队伍,抽水泥厂的人时,厂长派了小山,厂长说小山会写。今天小山回槐树沟,怀里揣着县法院给何大流的判决书。县上在清理群众申诉案件时发现多年来何大流一直在申诉,多达几十次,于是法院对何大流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当时的现场记录中明确写着作案现场有两个男人的脚印,与何大流当时交待的他把茶花抱进苇园后听到有苇子响动而逃跑相吻合,加之何大流多年来申诉不断,故断定在现场留下脚印的另一个男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复查中,认定何大流犯罪证据不足,改判何大流无罪。小山回槐树沟的任务就是给何大流送判决书。 小山回到家见过爹娘,拿了一包“黄金叶”来到二喜家。 “二喜叔。”小山走进院子里喊了一声,二喜答应着随即开门。二喜的屋里生了一盆火,由于柴货太湿,浓烟塞满了屋子。 “哎哟,是小山,快进来,快进来。”二喜一只手揉着被烟呛得直流泪的眼睛,一只手拍打着落在小山身上的雪花儿。 “范娃哥。”小山进屋后才看见坐在火盆边被浓烟裹着的范娃,高兴的说:“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小山,快坐。”范娃坐着没动,伸手在墙边拉过一根小板凳。“路上雪大吧?” “大。路上的雪有一两尺厚。”小山说:“大脚婶呢?” “在那个屋偎被窝呢。”二喜说:“这回回来总该耍两天吧?” “耍不成,明天就得走。”小山说。 “急啥?这么大的雪,在家住一夜,还不如不回来。”二喜说。 “有事儿。这回回来是专门给大流叔送判决书的。”小山说。 “都判了十几二十年了,监也坐够了,咋着这阵儿又给他送那东西?”二喜不解地问。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大流叔被平反了。”小山说。 “有这种事儿?咋平的反?”范娃问。 “大流叔是冤枉的,他没有罪。”小山说。 “没有罪?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没有罪?”范娃瞪着两只大眼睛。 “这是法院复查后做出的判决。”小山说。 “这就日怪了,当年不也是法院做出的判决?”范娃说。 小山掏出“黄金叶”递给二喜和范娃,范娃从火盆里拿起一根燃烧着的小木棍儿给二喜点着烟,然后问小山:“你不吸?”小山摇摇头。范娃把自已手上的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现在的事情说球不清。右派分子改正,地主分子摘帽,连何大流这种人也球平反,事情全球颠倒了。”范娃不住地发着牢骚。 二喜闷闷地吸着烟一声不吭。 “范娃哥,不是现在把事情搞颠倒了,是以前把有些事情搞颠倒了,现在重新颠倒过来。以前咱们小,不知道,二喜叔肯定知道。这回我参加落实政策,听说了不少事儿。就说大跃进吧,有人说大跃进有些盲目蛮干,或提了一条意见,或说了一句错话,就给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光这你说全国得有多少右派?难道他们真的就是坏人?我给你说个例子。水泥厂的老厂长有一次到车间检查工作,发现几个年轻小伙子躲在一个角落里打扑克,厂长说,你们要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活就只有饿肚子。反右运动一来,有人说厂长说社会主义要饿肚子。厂长说我没说过这话,我是说不好好干活只有饿肚子。那人又说,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你说要饿肚子,不等于是说社会主义要饿肚子吗?就这样,厂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职也被撤了,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厂里又把他抓回来斗争,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关在一间小屋里,寒冬腊月连被子也不给,只给他丢了一捆稻草,他受不了,也想不通,裤腰带一解上吊了。你说象这样的人冤枉不冤枉?该不该平反?” “象他这,当然该平反。他本来就不是坏人。”范娃说。 “我再给你说个例子。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是河东的。有一回他在广播里听到林彪讲话,林彪讲话声音拖得很长,有一句话林彪连着咳了几声,一句话断成了几节,他说林彪的喉咙象被球毛卡住了。就这一句话,他被判了死刑。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他不服,进行申辩。说他说话带把惯了,不是有意的。但谁听他的?谁敢说他不是有意地恶毒咒骂?枪毙的时候还怕他乱说,把嘴都给他缝上了。象这种冤案的例子还有很多。” “想不到还有这种事儿。”范娃说:“可是,小山,我跟你说实话,何大流的平反我还是没想通。” “范娃哥,大流叔的案子肯定弄错了,不然法院也不会改判。” 一直没有说话的二喜这时说话了。“我看是党和政府决定的都没错。过去是党和政府给右派和地主分子戴的帽子,那时戴是对的,现在党和政府决定给右派和地主分子摘帽,现在摘也是对的。案子判错了,冤枉了好人,也应该改。大流哥一直都在喊冤,判刑那天我也在场,他在法庭上大呼小叫,满口都是冤枉,连嗓子都喊哑了。没有冤枉他也不会那么喊。前几年他一直都在申诉,你还给他写过不少状子。” 小山问:“大流叔现在咋样?” 范娃说:“咋样?还不是在坟里。” 二喜说:“这几天一直在下大雪,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小山说:“那咱去看看他,把判决书给他送去,叫他高兴高兴。” 范娃没说话。 二喜说:“中。” 小山伸手去拉范娃,范娃吃力地站起,说:“我不去。” 二喜说:“走吧,好赖他也算是你叔。” 范娃说:“啥叔不叔,我从来就没把他当成叔。” 小山说:“走吧,范娃哥,就算你陪我。” 小山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范娃不好再推辞,就拄着拐棍跟在他俩的身后。 雪停了,银色的世界白得耀眼。坟地上个个坟堆尤如座座银山。何大流的墓口敞着,周围堆满了白雪,一个黑糊糊的大口朝着灰蒙蒙的天,就象一个深藏在地下的魔鬼张着血瓢大嘴要吞掉世界上每一个活人。三个人站在何大流的墓坑前,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人活到这个份儿上,真不如早点儿死去。他们看见堵在墓室门口的玉米杆东倒西歪,玉米杆的缝隙里露出一只干瘦发黄鸡爪似的手,一种不祥的感觉顿时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大流哥,大流哥!”二喜大声喊叫。 墓室里没有任何回音。 “大流叔,大流叔!”小山也跟着叫了两声。 墓室里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范娃,你站在这儿等着,我跟小山下去看看。”二喜说。 二喜拉着小山的手慢慢地走下墓坑,走近墓室,捞开堵在墓室口的玉米杆,两人顿时大惊失色,目瞪口呆。何大流爬在地上,头向着墓室门口,一只手伸向墓室外。那只手长长地伸着,象向别人要吃的,或者是想要口水润润干渴的喉咙,又象是在向法院讨要公道…… 二喜伸手摸了摸何大流的额头,已经冰凉冰凉的了。二喜把手背贴向何大流的鼻孔,连一点气息也没有了。二喜又拉了一下何大流的胳膊,那只早已僵了的胳膊象冰棍一样梆硬。 何大流死了。但他的眼睛还睁着,象两个玻璃弹子一样放射着冰冷的光。 “你俩在这里等着,我回去拿铁锨。”二喜走出墓坑对范娃和小山说。 范娃和小山同时点头。 二喜扛来了两把铁锨,胳肢窝里还夹了翎新席。二喜和小山把何大流抬到他睡的位置,把那翎新席盖在了他的身上。 “二喜叔,大流叔的眼睛咋还睁着?”小山怯怯地问。 “老年人说,人受了冤屈,死的时候眼睛都是睁着,这叫死不瞑目。” “那大流叔肯定是受了冤枉。” 二喜掀开席子,把何大流的眼皮往下抹了抹了,但那眼皮象用席篾儿撑着,怎么抹也抹不下来。 “二喜叔,咱把法院的判决书给他压到头下。” “中。这倒是个办法。” 二喜抬起何大流的头,小山把判决书放在他的头下。二喜再次抹何大流的眼皮,轻轻一抹,何大流的眼睛就闭上了。小山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流叔知道了。”小山说。 “他知道了。”二喜说。 小山和二喜从墓坑上来,一人拿着一把铁锨把挖墓时挖出的土一锨一锨填进墓坑,还堆了一个坟堆。 范娃的腿不得劲儿,拄着拐棍一直站在旁边。他见坟堆堆起来了,问:“小山,大流叔的判决书呢?” “压在他的头下埋了。”小山说。 “你不是拿回来了两张?”范娃又问。 “那一张在二喜叔那里。”小山说。 “二喜叔,你给我。”范娃说。 “你要那弄啥?”二喜问。 “我有用。”范娃说。 二喜从口袋里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判决书交给范娃。范娃在衣裳上拆了一根白线把判决书绑在他的拐棍上,一瘸一拐地走到坟堆前,恭恭敬敬地把拐棍插在坟堆上。 “我给他做了一个幡儿。”范娃说。 何家的坟地里出现了一座新坟,坟头上插着的那根幡儿上的白纸在寒风的吹动下象风筝一样不住飘荡,瑟瑟发抖。 “唉,咱村又少了一个人。”二喜说。 “又少了一个人。”小山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