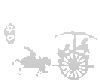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香炉咕喽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风来了!”稿纸都叫了;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的静物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果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主人咬着烟斗迷迷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在诗集《死水》中,这是唯一一首真正轻松幽默的诗歌。
闻一多整日伏案工作,无心料理生活事务,以致连他自己的书桌也堆得乱七八糟。偶而搁笔的闲遐之时,诗人打量这一片“惨不忍睹”的世界,倒觉出了许多乐趣来。在他眼里,所有的用品、杂物都仿佛“人格化”了,他们互相指摘、彼此嗔怪,好不热闹。
墨盒因没有了墨水而呻吟,靠近窗边的字典因被雨水渍湿而叫喊,卷曲着的信笺发牢骚,塞满了烟灰的钢笔怨声载道,还有,被火燎着了的毛笔,受挤压的铅笔,还有,香炉、大钢表、稿纸、笔洗、桌子、墨水壶等等,没有一件什物表示满意,他们异口同声地向主人抗议!
诗的幽默效果是怎样产生的呢?
幽默的首要条件就是心境的放松。在一个紧张的危机四伏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被引向了对自身生存的关注,他无法超脱,也就无法获得心的松弛。肮脏不堪、触目惊心的“死水”是这样,风云翻滚、雷鸣电闪的“长城”也是这样。书桌虽也是一个肮脏的、触目惊心的,甚至也是有点“风雨交加”的世界,但任何读者都不会把他们与我们的实际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闻一多也绝对没有类似的暗示。书桌就是书桌,与我们的人生境遇无干,我们足可以居高临下的来品评它、打量它,为它上面的居民们的互相攻讦而捧腹。
此外,幽默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不和谐的、出人意料的现象。比如,火柴本是诗人点烟之物,但是却偏偏燃着了毛笔,“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牙刷显然该是盥洗间的物品,却又在书桌上压住了铅笔的腿,至于香炉,本来就不该在书桌上占一席之地,不曾想它倒嘟噜起来“这些野蛮的书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最后,幽默还来自于诗人本身的自嘲精神。讥笑他人是讽剌,而嘲弄自己则是幽默。没有真正地从生存的泥淖中挣扎出来,就不可能有嘲弄自我的胆量,也不可能有嘲弄背后的机敏和洒脱。在这首诗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诗人的自嘲精神。不言而喻,所有的“肮、坏、差”都是闻一多本人一手所为,但他却津津乐道地表现着这一片的混乱,毫无愧色地转述着“居民们”对他这个主人的指责,末了,还笑嘻嘻地解释一番,抚慰一番,实在是颇有智者风度!
这首诗因其轻松幽默而与闻一多《死水》中的其他篇章颇为不同,我们看到,当诗人步入社会,思考人生时,他是痛苦的、迷惘的,当他退入书斋,沉湎于学术时,他又是充实的、温和的。人不能永远把自己浸泡在苦水里,他得有自我调剂的时候。《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收束了诗人的《死水》诗集,以后,他真地长时间里独坐在书桌之旁,进入到所谓的“向内发展”的时期。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