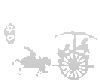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烂果
我的肉早被黑虫子咬烂了。
我睡在冷辣的青苔上,
索性让烂的越加烂了,
只等烂穿了我的核甲,
烂破了我的监牢,
我的幽闭的灵魂
便穿着豆绿的背心,
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
《烂果》收入《红烛·孤雁篇》,是诗人留美时所作。
这首诗以自叙的方式,生动地表述了一只正腐烂的水果渴望心灵自由的要求。它的心受着两层外壳的监禁:最外层的果肉和中间的核甲。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它落在了“冷辣的青苔上”,虫子咬烂了果肉,第一层监牢打开了,第二层监牢也正在被啄破,光明和自由就要来临,水果想到这里,不由得充满了喜悦……诗歌很可能是诗人对某一次见闻的提炼,有点类似于古诗中即景赋得的味道,只是换了叙述的角度,情调上也趋于幽默风趣。
但这只是诗的表层的意蕴,在中国诗歌艺术(包括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实在并不存在真正的咏物诗,中国诗人笔下的物都与人息息相通,甚至是取了“物”与“人”相通融的某一中介点。这时候,物非物,而人非人。这只“烂果”亦如此。你看,层层叠叠的束缚、囚禁,心灵被紧紧地包裹住了,不得光明,不得自由,这不正是中国传统式的心灵么?
《烂果》生动地描述了传统中国人的封闭的灵魂和盼望自我解放的愿望。
应当说,作出这样的认识、萌生这样的愿望都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生存环境关系甚大。
心灵的封闭是与襟怀的开放相对而言,没有“开放”的参照就无所谓封闭,没有“开放”的刺激也无从产生自我解放的需要。《烂果》的诞生只能是在“五四”以后,而诗人当时所生活的美国社会又从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象,当闻一多这样一个素来谨慎克制的中国青年来到这样一个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大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里的一切生活方式,包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都与我们熟悉的中华社会那么的不同,陌生、不适,但你最后不得不承认,在洒脱、放任、浪漫的西方民族面前,文质彬彬的中国人过于拘谨、过于自我束缚、过分封闭了!尽管在同一时期,西方文化的威压曾促使闻一多举起了“文化国家主义”的旗帜,但对于这么一位忠实于自己感受的真诚的诗人而言,他不会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实际人生体验。《烂果》就相当真诚地表现了诗人敢于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的精神。
果实的封闭不是某种外来压力的结果,是“我的肉”和“我的核甲”这双重的自我作用,(不妨可以想得多一点:这双重的自我作用原本是为了自我保护!但不知不觉当中,保护也就成了一种束缚,而我们也常常因“保护”而忽略了这样的束缚)果实要挣脱的就是这类自我的力量,自我解放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抗争的过程,自由的蜕化必然经过自我彻底腐朽乃至毁灭,只有陈旧的自我被消灭了,果实才可能获得解放,而一个崭新的自我才可能诞生,这是生命运动的规律。当然,旧我的毁灭也是需要有胆识、有毅力、有决绝的勇气。
“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是理性的,而“烂果精神”则是感性的。两者的尖锐冲突在诗人后来的《死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烂果》一诗则属于早期“烂果精神”的萌芽,在这里,矛盾冲突的特色还并不明显,诗人是以心灵去感受人生,又无所顾忌地抒写着这种瞬间的感受,各种不同的情绪还没有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心理层次上去甄选、比照、揉搓,所以从总体上讲,倒相对的显得单纯一些。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了“烂果”这一物象的第一人称方式(即所谓“客观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这固然是便于烂果的自我阐述、自我表现,从而生动地呈现了一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就符号学的角度讲,“我”在实事上所代表的烂果与这一符号所暗示的诗人本身也构成了某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联系,“我”游离于真实的“烂果”与诗人之间,从而扩充了语符自身的丰富性,强化了诗的立体性,给以人充分的“主体投入”的可能。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