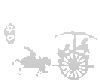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我是一个流囚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金甲紫面的门神
举起宝剑来逐我;
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
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忽地一座壮阁底飞檐,
象只大鹏底翅子
插在浮沤密布的天海上:
卍字格的窗棂里
泻出醺人的灯光,黄酒一般地酽;
哀宕淫热的笙歌,
被激愤的檀板催窘了,
螺旋似地锤进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觉轻去一半,
仿佛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啊快乐──严懔的快乐──
抽出他的讥诮的银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乐底罪人,
幸福之宫里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这里随便打溷呢?走罢!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
唉!但是我受伤太厉害;
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
我的鲜红的生命,
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这是一首寓言性的诗作:一位被人放逐的流囚,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没有欢乐、没有希望,他步履迟重、足下鲜血淋漓。这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画面,而是诗人某一精神体验的形象化表述。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解读它的内涵。
其一,这个流囚“年壮力强”。这四个字生动地道出了“我”的青春焕发,热血沸腾。“我”的生命力正处于极度旺盛的上升时期,生活对于它当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我”需要人生、需要快乐,也有无穷无尽的勇气,有用之不竭的精力,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碍他去追求、去奋斗。但是,成为“流囚的竟然就是我”!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囚徒带给人的是那种悠长的凄凉感,而“年壮力强”与囚徒的身份联在一起又给人强烈的压抑,乃至气闷的感觉,一个年青的生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力,这无论怎么说都是残酷的。
其二,这也不是一般失去自由的囚犯,而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流囚”。“流”似乎给了他一些自由,可以不必如另外一些犯人那样被拘禁在牢狱里,过着终年不见阳光的生活;但是,“流”所给予他的相对的自由并不比他因此而遭受到的苦难多,当“我”的前方一片茫然,没有任何的生机,当“我”永远都不能再步入途中的任何一处温暖的居所作短暂的休憩时,“流”就意味着眼睁睁地流向死亡,而且这还不可能是那种痛苦淋漓的猝死暴亡,死将是悠长的、慢腾腾的,需对那“鲜红的生命”一滴一滴的耗尽……流浪者也许是“自由”的,但自由闯荡在茫茫天地间竟又永无获救的希望。这又是怎样的自由呢?
如果将第一个方面与第二方面综合起来看,那么“我”的遭遇就更是不幸、更是苦涩的了。那么,这样的辛酸又象征着闻一多在当时的什么样的精神体验呢?该诗作于闻一多刚到美国留学之时。1922年9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讲到了这首诗的缘起。他说;“《我是一个流囚》是卢君之事所暗示的;卢君之事实即我之事。”卢君与闻一多是清华校友,也爱好文学,但因不惯异国生活,精神上受到了不少刺激,以至发疯。这可以说是当时一代青年人的普遍现象:初涉人生长途,孤独、寂寞以及对未来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这种心情与诗人作为“五四”青年那特有的“年壮力强”相对应,形成了诗人内心体验的复杂性,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年壮力强”而对人生世事怀着自己独立的理解。这些人生观、世界观又在当时显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于是,那种强烈的流浪感、被放逐感就产生了,诗人不知不觉地便以“流囚”自居。
被放逐感、流浪飘泊感,这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体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哲学家都自称自己时常笼罩在强烈的“被抛弃”、“被放逐”的体验之中,漫长的漂泊之路横亘在他们面前,又向着无限的远方伸展开去。当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囚”群落中,闻一多的体验还是颇为与众不同的。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闻一多的独特性。
其一是流囚自我的清白感。贯穿这首诗始终的是这样一个自白:“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这无疑就是对这不幸命运的抗议和控拆。在他看来,自己是清清白白的,本来就毫无罪过,可见,放逐是现实社会对他的残酷迫害。清白的自我与污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我清白必然也是个人与现实两相对立的结果。与之相应的背景是:个人向社会争夺生存权利,社会以其整体的传统力量压制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又已经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他敢于公开维护自己的利益,他非常清醒、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理想的正义性。所有这些都属于“五四”文化背景之产物。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方法及道德范畴中进行了新的革命,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但是,作为专制的统治,作为愚弱的国民却显然在整体上构成了巨大的传统性力量,从各个方向上完成着对先知先觉者的包围和迫害,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只是道义上“清白感”。
这是与二十世纪“流浪意识”的重要区别之所在。西方二十世纪作家几乎都不再为自己的什么“清白”而辩护,他们所要反复强调的是他们“流浪”中的重重精神苦难,是不断的对真理的探寻及其不断的失败。在这里,道义的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并非社会的传统力量对个人的压制和迫害之结果,而是先觉先知的精英分子在超越历史、超越人群之后的一种茫然失措,在这个时代,重要的问题都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着讨论和对话,道义性自慰早已成为了遥远的历史。相反,由于宗教意识的复活,他们还很可能自虐般地宣布:我有罪!我应当接受上帝的惩处。当然,这罪也不是道德性的,而是他为肩负苦难而选择的精神支点。在西方文学史上,自我清白感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初期一些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之中(包括卢梭),而中国“五四”文化背景从本质上讲更具有与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相近似的特点。
其二是放逐流囚的是他周遭的人们。用诗中的话说,就是“他们”,那些住在“幸福底朱扉”后面的人。这里暗示了一个“家”的意象,“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我”所受到的迫害固然是社会意义的,但又还不是西方十九世纪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社会的“具体细胞”──人伦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人伦关系决定了所谓“社会”的一切实质性内容,所谓社会的迫害其实也就是人伦的破害(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在本质上是没有“社会”的)。迫害的方式也是“人伦型”的:剥夺他享受人间温暖的权力,把他拒绝在所有的“家”门之外,那么,失去了“家”的中国人就失去了灵魂,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你看,诗中写到,“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黄昏,在这个时刻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正匆匆地赶回到他们的巢穴之中,但“我”却被“推出门外”。古人旅行在外,见日落西山,小桥流水尚且生出思家的怅惘,何况是被永远的赶出家门呢。至于途中浮现的“家”的幻景就分明更是对“我”有意的讽刺和侮辱了。我们只有扪心自问,家在我们的人生中究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然后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受到如此厉害的内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这漫长的漂泊之途中,真正引起诗人恐惧的还不是死亡,不是未来的黑暗,而是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特征的东西:他永远失去了人伦的归宿──家。
人伦,是解读中国现代悲剧的一把钥匙,也正是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精神的民族内涵。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