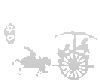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游戏之祸
我酌上蜜酒,烧起沉檀,
游戏着膜拜你:
沉檀烧地太狂了,
我忙着拿蜜酒来浇他;
谁知越浇越烈,
竟惹了焚身之祸呢!
看了这首短短的六行小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联想到前面曾出现的那首著名的《风波》(原名《爱的风波》)。在《游戏之祸》中,诗人再一次重复了《风波》所描绘的痛苦体验,从字面来看,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没有爱人那“明亮的笑焰”来把“我”的泪水“晒干”;而“我”也不仅仅是“障瞎了双眼”,而是在鲁莽戏闹的行为中自食其果,导致了引火烧身的惨祸。
在诗人所处的“五四”时代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期,风云变幻、动荡不息,一切旧有的观念、思想和行为习惯都在改变,而新的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思想体系却还没有确立。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天真无邪、缺乏经验的青年人必然感到无所适从。他们靠自己的才力在茫茫社会中寻路,一时找不到正确坦直的途径,受到一些挫折甚至磨难,本来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游戏之祸》所暗指的事件却不是这样,作为叙事主体的“我”,不是由于幼稚天真,而是由于对人生的戏谑和嘲弄,以“游戏”的态度燃沉檀,浇蜜酒,最后引火烧身,“竟惹了焚身之祸”。一方面,“我”是无知的,值得怜悯的,只迷惑于沉檀和蜜味表面的香气馥郁,甘醇甜美,竟不能揭开这虚幻之美的面纱,去看看那“香”与“美”背后所隐藏的奸险和丑恶。于是,“我”成了无知和鲁莽的牺牲品,“沉檀烧得太狂了,/我忙着拿蜜酒去浇他;/谁知越烧越烈,/竟惹了焚身之祸呢!”在这里,“沉檀”正如在《风波》中一样,仍象征着一种具有伤害性的邪恶势力,它芬芳馥郁的香味其实是障害人的精神与肉体的陷阱。对于无知幼稚的青年来说,它的形象如此可爱可亲,以至当“我”游戏着“膜拜”情人时,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沉檀”作祀品,在这种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沉檀的“毒火”肆无忌惮地狂燃起来,其危险性也就更加明显。同样,蜜酒象征着酿成“游戏之祸”的催化剂,它加剧了沉檀火势的威力,最终将“游戏”人生的“我”吞噬了。如果说“沉檀”是物质上的有害因素;那么蜜酒则是精神上的麻醉剂。蜜酒和沉檀构成了损害青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魔力,全面象征了当时社会的邪恶势力。然而,沉檀和蜜酒还并不是诗人构筑全诗的主旨,而诗人的良苦用心还在于提请人们吸取来自于“我”的“烧身之祸”的教训。我“与”《风波》中的执着爱之追求的抒情主体不同。“我”是一个与世界疏离、徘徊于自己小天地的个人主义者,“我”不仅没有追求理想的狂热信念,而且以游戏人生,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对待一切,不论烧沉檀、浇蜜酒,还是膜拜心中的情人——“你”,都是随随便便,信手为之,既不选择恰当手段,又不考虑事情后果,直到最后引来“焚身之祸”,“我”仍没有完全清醒,更没有认清事件发展的本质。“我”是“五四”退潮后生活在迷惘、无聊,麻木中的相当一部分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们没有明确的理想,没有正确的手段,仿佛是漂浮在大海上没有航向的孤船。然而,他们又不甘寂寞,希望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他们采取一些轻率、鲁莽、毫无意义的行动,以游戏的态度嘲弄社会,也嘲弄自我。诗人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游戏态度的巨大危害,巧妙地以诗意形象加以表述,以唤醒那些仍在孤独寂寞中游戏人生、时时面临着“游戏之祸”的人们。(阎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