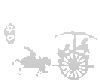闻一多诗选
黄昏
太阳辛苦了一天,
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面通红,
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黑黯好比无声的雨丝,
慢慢往世界上飘洒……
贪睡的合欢叠拢了绿鬓,钩下了柔颈,
路灯也一齐偷了残霞,换了金花;
单剩那喷水池
不怕惊破别家底酣梦,
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饭后散步的人们,
好象刚吃饱了蜜的蜂儿一窠,
三三五五的都往
马路上头,板桥栏畔飞着。
嗡……嗡……嗡……听听唱的什么──
是花色底美丑?
是蜜味底厚薄?
是女王底专制?
是东风底残虐?啊!神秘的黄昏啊!
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
这辈嚣喧的众生
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黄昏》是一首现代写景诗。
说它是“现代”的,当然就是与传统的写景诗比较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比较当中,我们才将发现《黄昏》所描绘的“黄昏”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黄昏曲”比比皆是,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肃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当然,《黄昏》所描绘的是现代都市的黄昏。你看,这里有合欢花、路灯、喷水池以及在马路上溜达的人群,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都市风光,与王维的大漠、长河相去甚远。中国古典诗歌的黄昏多是荒漠乡野上的景色,但是这样纯粹取材对象的不同还不足以说明闻一多那独特的诗心。
我认为,《黄昏》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是它那轻快乐观的情调:辛苦的太阳终于到了下班休息的时候,它高兴得满面通红,急不可耐地结束这最后的旅行。路旁的合欢因“贪睡”而显出几分惹人怜爱的模样;路灯“偷了残霞,好一付顽皮的姿态;喷水池更是“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闲散的人群“好象刚吃饱了蜜的蜂儿”一样哼哼呀呀地唱着小曲。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黄昏”大都是人生衰败体验的投射,弥漫着愁云惨雾、凄风苦雨,属于中老年文明的审美景象,闻一多的“黄昏”则浸透了生命的意趣和节律,满怀少年人的好奇,属于青年文明的审美意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唤发的青春热情在《黄昏》里光彩夺目。
除了时代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投影之外,这一情感基调上的差别也与诗人的特有的抒情模式有关。中国古典诗人的抒情大都属于与现象界的一种“共鸣”模式,即诗人与现象界互相渗透、融合,彼此连接,这样,自然节奏的轻重缓急、抑扬起伏都直接转化成为了诗人的内在感情。黄昏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其特殊的地位在于:它是黑夜将至、生命沉寂的过渡期。同清晨万物苏醒、百鸟争鸣相比,同中午赤日临空、生命奔流相比,黄昏都显得过分颓靡,而失去了催人进取的活力。农夫荷锄、牧童扬鞭,那是匆匆赶回家去休憩;群鸟横飞,那是急切地寻找巢穴,也许晚霞还是绚烂多彩的,但古人早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而闻一多显然并没有把自己嵌入“黄昏”的生命节奏中去,所以在他眼中绝没有生命蛰伏的预兆,没有黑夜降临的孤独。他牢牢地站在一个与自然相区别的立场上,仅仅相信自己个人的思想意识。于是,现象界的黄昏就完全独立为外在的景致,而他则是这一景致的旁观者、品味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风景,清爽怡人、旭日东升的清晨是美丽的;凉风习习、变幻不定的黄昏也是迷人的,即便是漆黑如墨、寂然无声的夜晚也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妙处。在现象界里取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了诗心过早地陷入传统模式的窠臼,摆脱了“老气横秋”的天性,属于青年学子本身的求知欲、进取心与青春浪漫的激情溢满诗章。
由此也决定了《黄昏》的第二个重要特色:人格化的自然物象。
在《黄昏》中,不仅活跃着的人的形象处于诗的中心,而且其他的自然物象也染上了鲜明的人的色彩。改变其“本然”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物象人格化。如诗人开门见山的一句“太阳辛苦了一天,/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喜得满面通红,/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这样写太阳,在古典诗歌中还不曾有过,在现代新诗中也并不多见,他显然来自于另一诗歌文化系统的影响。如雪菜谓云雀“象一位名门闺秀,/索居深宫”,济慈言星星“象一名大自然的坚忍不眠的隐士,/睁着一对永远不闭的眼帘,”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新诗中,《黄昏》显示了相当成功的“化欧”、“化洋”的能力。
诗人主体意识的强化以及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也是《黄昏》突破传统诗歌意旨的关键因素。“物态化”诱惑诗人去寻觅自然细微的节奏,古典诗歌的“黄昏曲”重在渲染黄昏时分物我感应产生的特殊氛围、意境,它反对诗人在这个氛围中作过多的追问和思索。《黄昏》显然也背弃了这个传统,全诗的“诗眼”恰恰在那一连串的追问之中,最后归结为一个难以回答的又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问题:“这辈嚣喧的众生/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这种追问颇有点西方泛神论的味道:自然的“真义”并非我们的感官就能体验和理解的,自然毕竟是与人类的意识结构相区别的另外的一个实体。
闻一多的《黄昏》为中国现代写景诗树立了全新的榜样。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