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主 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编辑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时间:1994年8月
董事長致詞
深圳南亞實業集團(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全民所有制原型為基貌、成功地進行著所有制改造,並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2000萬元人民幣值資產,而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以此持股和控股的公司。
公司同仁明白,經濟要發展,首先要有先進的推動經濟發展的創造性動力和推動科學發展的哲學思想。中華民族正面臨著怎樣用東方文化與現代科學結合,解決人類追求富裕和實蜆富裕以後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是非界定危機的轉折關頭,這是當今企業文化最深刻、最重要的內涵。
經濟和文化是人類生命的兩翼。二者相得益彰,稍偏則覆。我們嘗有一自覺有趣的“企業管道說”,認為:生之為人,帶著企望、貪圖(多以建立功業為目標)在“舉踵也”之後,即進入了人生的一段管道。這管道的上沿是成功,下沿是失敗光滑的管壁愁於攀緣。失敗固然沮喪:成功呢?實證的體驗來說,更多的是一段過程走完的迷茫和新過程未開始的困擾。而在其間人們又在幹什麼呢?在為了得到而處心積慮,擔心失去而憂心忡忡。人生如斯,生命則在此扭曲,人格則在此分裂,物質創造的動力則在此衰退。經濟也因精神動力的衰退而進展遲緩。因之,經濟的衰退,終究是哲學的衰退,文化的衰退。
如何能讓人類在失敗中不那麼沮喪,在成功中不那麼失望。成功、失敗之間,能夠“得之不甚喜,失之不甚憂”,讓生命踏著穩健的物質創造步伐前進,這是一代文化人的神聖使命。
為此,我們寄希望於東方中華文化在21世紀為振興現代經濟與現代文化的歷史嬗變中扮演重要角色。害希望於《中國文化》在已有國際聲譽的基礎上,更加深入,直指人心。乃加盟本刊,與之合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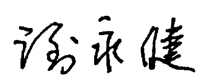
謝永健
一九九三年三月六日
編 後
這是第十期。《中國文化》已經創刊五周年了。
當本刊初創的時候,我們的願望并没有這樣奢侈,以為出版五期、六期,就已經很不錯了,誰知今天居然能夠以特大號慶賀她的五歲生日。五年十期,不足四百萬字,其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有關問題所作的探討的局限,可想而知,已經做的和想要做的、能夠做的之間,尚有好大一段距離。略感欣慰的是,辦刊過程中實踐了我們在創刊詞中申明的宗旨:“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標其异。”後來又概括為四句話:“深研中華文化,闡揚傳統專學,探究學術真知,重視人文關懷。”這一辦刊宗旨得到了海内外眾多學術同道的支持和響應,作者、讀者和编者一起把《中國文化》當作了實踐自己學術理想的一塊園地。
為了紀念《中國文化》創刊五周年,這一期特發表本刊主編與余英時先生的長篇訪談錄,訪談時間在1992年秋天,圍繞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重建逭一總題目,從學術的視角切入,涉及到思想、學術、文化、社會、歷史、人物諸多方面,不少問題是當前的文化熱點和學術難點,余英時先生快意地系統地發表已見,不乏發以前所未發、道别人所未道的妙語哲思,使得這篇訪談非常珍貴。而且與他的《章學誠文史校雠考論》一并刊出,相信會引起學術界同道的興趣和關注。
本期“文史新篇”專欄刊出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字,這在我們實屬一個特例。自創刊以來,只在第五期發表過已故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寫於二十年代的一篇《紅樓夢辨序初稿》,因為該稿用很大的篇幅講學術史,被葉聖陶先生批評為“說國故太多,而紅樓夢太少”,而這正是本刊所取意處,非關紅學也。這次何炳棣教授的《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测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是一篇史學家作出位之思而頗具創意的正宗紅學文章,足可令嘈雜擁擠的紅學界耳目一新。我們寧願破此一例,也認為有必要推薦給讀者。
“專學研究”欄里關於帛書、甲骨學、敦煌學的幾篇研究文字,都有相當的學術深度。李零先生的《楚帛書再認識》,第一次詳盡介紹了楚帛書流散到美阈的具體經過,對帛書的種類、形制、圖象、文字和同時出土的帛書,作了綜介研究,提出不少新的看法。此外,龐樸的《談“玄”》、閻步克的《王莽變法與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都是讀書得聞、好學深思之作。余秋雨的文章,對昆曲這門最高雅的藝術給以文化學和戲劇美學的恰當定位,稱昆曲是傳統戲劇學的最高典笵,論述得有物有則,值得一讀。
關於明清文化思潮的一组文章,互有連帶性,從不同的側面揭示出中國歷史上文化轉型期的思想文化的一些特征。我們今天正處於從混沌到有序的新的歷史轉型期,昨天之象可以映合今天之象。恰好湯一介先生的《論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合力》,對逭一問题從文化理論上作了闡證和說明。孫康宜、樂黛雲兩位教授的文章,論述的也是明清文化現象,只不過所舉證的是文學創作。而“現代文化現象”專欄《張東蓀舆民主主義思潮》一文,儘管主要是對張氏著作文本的疏解,亦可見出東西方文化激蕩中知識份子理性的張揚。
錢穆先生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在本刊第四期刊出後,學術界反應熱烈,季羡林、周汝昌、蔡尚思諸先生嘗進一步為說,但也有不同意見。這一期杜維明先生從剖解季先生的回應入手,稱錢作為“晚年定論”,是“從其畢生學養中提煉出來的智慧結晶”,是一篇藏有“大體悟”的“證道書”,須得有“實有諸己”的精神,方能微窥其妙,非王陽明所斥責的“稍能傳習訓詁,即皆以為知學”的“世之學者”所能理會。余英時先生和本刊主编的談話,也接觸到了這個問題。
“域外漢學”專欄里,柳存仁先生以詳盡的资料,介紹了馬來西亞漢學的歷史和現狀,這是1993年11月作者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國際漢學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題演講。李明濱先生的文章,介紹了不久前俄國召開的一次漢學會議的情形,表明俄國漢學家在重新評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頗耐人尋味。
王世襄先生的“舊京風物”系列,以其絕活绝作,倍受讀者激賞,我們已刊出《秋蟲六憶》、《獾狗篇》。這期又刊出《大鷹篇》,以饗讀者。“序跋與書評”專欄刊載的程千帆、馮其庸、黄翔鹏、王蒙四位先生的文章,也都是名家名篇,值得賞讀。
這一期只有一篇文章對本刊來說迹近破體之作。造就是王悦的《女人和酒》。作者是一位曾在大學任教的女教授,退休後皈依佛門。文章潑辣生動,直抒胸臆,空諸依傍。難能之處在於確實梳理出中國文化精神軌迹的一個側面。徵引之材料雖或為文史專家所習見,但習見者不一定留心,在作者筆下统為一綫所貫穿,化作山澗流響,為歷史作不平之嗚。
我們希望這本為慶賀創刊五周年出版的特大號,内容能夠比已往各期更豐富一些。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編後谨記
文章分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