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第29期(2009年春季号)
主 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编辑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时间:2009年春季号
學人寄語
光緒三十三年,清廷修律大臣沈家本將《大清刑律草案》進呈上奏,據時人紀云,此“草案一出,舉國嘩然”。盡因這部“專以折冲樽俎,模範列强為宗旨”的刑律草案太過西化,竟至動摇了二千年來人們奉為國本的禮教。
以張之洞、勞乃宣為代表的“禮教派”并不反對學習西方,變法圖强,但他們强調國情,以為各國禮俗民情不同,法律因之,所謂“天下刑律無不本於禮教”。他們更主張,變法之道,在立基於己,取人為用,而反對一味舍己藝人。而以沈家本、楊度為首的“法理派”則以大同之制、世界公例、進化之理為圭臬,嚴法律與道德之分,重公域與私域之别,欲以國家主義克服家族主義,以政法手段改造社會、再造文明。
如今,整整一百年過去,當年的激辯久已沉寂。歷史似乎是在“法理派”一邊:政治、社會、文化之革命鋒芒所及,儒家社會解體,基於禮教的文明秩序分崩離析;現代法制蔚為大觀,當年曾驚世駭俗的刑律草案早已不在話下;“國家主義”大獲全勝,“規劃的社會變遷”影響深遠。然而,在目睹和經驗了所有這些變革之後,我們驀然發現,當年的禮法之争雖然早已烟消雲散,但是隱藏其後的問題不但没有獲得解决,反倒在這個“進步”了的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法理派”夢想成真的時代,更加突出而尖銳了。换言之,那些緣道德主義與法律主義、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家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自然主義與理性主義諸論争而浮現的困擾,於今較以往更為深切,也更加難以抒解。
在過去的一百年裹,“法理派”的事業被人們發揚光大,但是從現在開始,“禮教派”提出的問題也應該被認真對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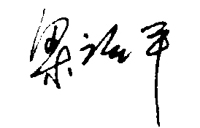
梁治平
2009年4月22日
编 後
去年年底,具體時間2008年11月30曰,本刊和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邀集了一次學術聚會,京城學界的老輩碩學和年輕友人多有參加。此期《戊子歲尾雅集記盛》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現場互動的諸種情形。聚會的請函作“戊子歲尾雅集小柬”,其中寫道:“中國文化研究所暨《中國文化》雜誌,今創立已二十年矣。時序遞嬗,歲月遷流,逝者如斯。古者論學,最重省切二義。省者返也.切者問也。省能忠信,問則致思。詩云:‘瞻彼淇澳,某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琢。’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易》‘文言,稱:“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孟子則曰:‘是尚友也。’故當此廿年回首返躬之際,擬誠邀京城師友宿學,於戊子冬初之月,月杪周休之曰,藉國際俱樂部飯店二層至尊廳,宴聚雅會,懇談論學。臺端向為本所本刊之學術護法,亦情牽道契之素友,特恭邀大駕撥冗光臨,或抵掌以談,或拈花而笑,要皆為中國文化之運命而有所思議,語默動静,貞夫一也。本所同仁豎本刊编友自當擁篲以待。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東中頗致省切尚友之微意。
雅集諸賢說了許多鼓勵的話,我們惶悚感激之餘備感珍惜,同時越發不敢懈怠,陳平原先生稱《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有性情。是文章,是學術,也是性情。樂黛雲先生也有如是看法。我們感到可謂知言。那么索性我們便提倡有性情的學術如何?以此,則清儒提倡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警則,固不能不守持,而錢曉徵告白於海內的“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以及陳寅恪一再標舉的“瞭解之同情”,亦未敢或忘。有物有則文章體,知情知義素心人。章實齋豈不言乎:“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悦以解也。”(《文史通義·知難》)承蒙海内外老師碩學和青年學術先進的垂顧,所幸本刊每期尚不乏名篇佳構,此似唯一可以告慰己心并報讀者呵護偏愛於萬一者。
本期柳存仁先生《金庸小說裏的摩尼教》一文,開啟了武俠研究和宗教研究的新生面。柳先生精通《道藏》,小說史和道教史是其專精的兩個域區,而尤以研究小說和宗教的關係享譽學林。寫於l985年的《全真教和小說西游記》,就是這方面的代表論著。他還出版過英文著作《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現在又通過對金庸小說宗教門派的研究,將摩尼教在中國傳布的情形作了一次歷史的還原,勾沉索隱諸多不經見的珍貴史料,融大眾欣賞的說部與枯燥無味之考據於一爐,雖不過四萬餘言,實為一绝大的著述。錢鍾書先生稱柳先生“高文博學,巍然為海外宗師”。余英時先生嘆美其治學精神則說:“他的著作,無論是偏重分析還是綜合,都嚴密到了極點,也慎重到了極點。我在他的文字中從來没有看見過一句武斷的話。胡適曾引宋人官箴‘勤、謹、和、缓,四字來說明現代人做學問的態度,柳先生可以說是每一個字都做到了。”但當世真知仁老博雅淵深之學者甚乏其人,故余英時先生致慨:“新史學家恐怕還要經過幾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認識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價值。”(見柳著《和風堂新文集》之余序,新文豐出版公司,臺北,1997)英時先生還披露,單是仁老多次閱讀《道藏》的筆記,就有數十册之多,真希望這些稀世珍奇之初始著述能够早曰印行面世。
范曾先生的兩篇新作《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没落》和《書道法自然》,亦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兩者實為姊妹篇,都是今年早春羈旅青島時所撰。他痛恨後現代主義藝術家以無休止的乖張褻瀆了神聖的“自然大秩序”,他說上帝已經在雲端向他們訕笑,并“抛下了詰問”。他無法容忍杜尚把蒙娜麗莎這位“文静而恬淡、高雅而質樸的古典美人”,變成“長出翹起的鬍鬚”的“神經質的達利”。他稱杜尚是“打開那帶给人類無休無止的瘋狂、罪惡、嫉妒和疾病的潘多拉魔盒”的始作俑者。他的文化理想是藝術和自然秩序的和諧。他說“人類歷史上所有精妙绝倫的藝術,無一例外的一定是與天地精神相往還的產物”。所以他高標“書道法自然”,對仰韶時期的彩陶圖形施以贊美:“那天真的,樸素的,質勝文而近乎野的造型,如日月山川人面游鱗等等,给我們展現了先民豐富心靈和强烈的表現欲,那是人類文明肇始的曙光。其中生拙和鮮活并在,懵懂與靈慧齊飛。”而書家之道,“至大之境必為本乎觀之於天,悟之於心,應之於手。揮寫之際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當此之時正所謂天人合一?略無間隙”。包括書道在内的干百藝事,在范先生看來,其最高境界應是藝術與自然秩序冥和,而新古典主義則是達致此一境界捨此不二的方便法門和微妙法門。
本期周勛初先生讀《文心雕龍》,來新夏先生讀《文史通義》,葉嘉瑩先生論宋代女詞人李清照與朱淑真,鄧小軍先生辨陶淵明甲子書法:范子烽先生探討中古的喉音藝術,揚之水先生發覆明代金銀飾品中的藏傳佛教,程毅中先生摭談雜賦與小說,均大家手眼,微言妙道,不勞贅語提撕。陳平原先生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回覲中國現代文學,蔣寅先生申論古典文學的精神史意義,亦為別具機杼的宏觀研究。桑兵先生發掘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以字源學和語言學詮釋古代思想的方法,張旭東先生綜合辨正陳寅恪先生“恪”字的音讀,理據充分,宜有可觀。謝泳先生的文章我們猶豫再三,還曾送請李零先生審閱,最後决定易名刊出。
馮其庸先生的《王蘧常先生書信錄》和舒蕪先生的談“荒蕪的輟筆”兩文,尤其要向讀者推薦。王字瑗仲,嘉興人,嘗師從沈曾植乙庵,淹通文史,國學根柢深厚,而以章草名家。1900年生於天津,1989年辭世於上海。馮先生早年就讀無錫國專,1947年開始師事瑗仲先生,長期書信往還,如今保存王的信函有五六十封之多。此次刊佈的十四封書簡,起自1965年,迄於1980年,均為章草書法,所附書影,狷雅盈箋。馮先生所作主背景說明,頗及半個世紀以來學界和學府的人文往事,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舒蕪文章的題目作《論“没意思”》,其實大有意思,謂:予不信,讀後可知。
2009年4月29曰编後記
文章分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