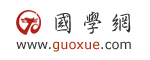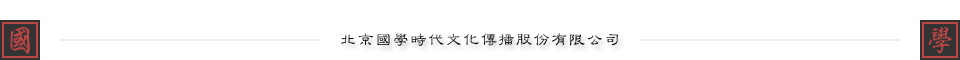《中国文化》第25-26期(2007年秋季号)
主 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编辑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时间:2007年秋季号
學人寄語
近代以來,分科治學,已成體制。新銳學人以分科治學為科學,其實分科究竟如何發生,尚待探究。要因之一,則為人的智慧體力有限,而知識無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分門別類,縮短戰線,使人力足以承受。可是如此一來,渾然一體的學問被肢解為彼此獨立的系統,久而久之,不僅各科之間相互隔絕,每科內部也日益細化。以史學而論,縱向分段,橫向分類,林林總總的所謂斷代、專門、國別史,大都不過貫通歷必備的條件基礎,揚之則附庸蔚為大國,抑之則婢作夫人。尤其是晚近史料繁多,超出人力所及,近代史雖然已是斷代,還要進一步細分化,時間上分段,空間上分類,形同斷代中的斷代,專史中的專門。縱橫兩面,相互隔膜,所謂占領制高點的專家之學,漸成割據分封,畫地為牢,而占山為王與落草為寇實無二致。
研究歷史,若一味用分科觀念,勢必以后來眼光看待前人前事,強古人以就我,符合后出外來的學科軌則,卻不理解前人的習慣作派。歷史本為整體,各部分有機聯系,近代學人重寫歷史,以及用西洋系統整理國故,還以斷代、專門、國別各史皆為通史一體,后來則視專攻為獨門,歷史的無限聯系補人為割裂,而所謂跨學科,則往往是坐井觀天,自我放大,或踉蹌跳躍,不守規矩,以局部求通論,以歸納代貫通,勢必以偏概全,看朱成碧。分科治學之下,學人的眼界日趨狹隘,沒有成竹在胸,難免盲人摸象,無法庖丁解牛,刻舟求劍,緣木求魚之事,日益習以為常,甚至天經地義。
博而后約,以專致精,由精求通,整體之下探求局部,仍為治學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門。如此,才能接續前賢的未竟之業,以免日暮時分盲人騎瞎馬行險道,將天邊的浮云誤認作樹林,或以找漏洞尋破綻鑚空子對着干為治學的正道坦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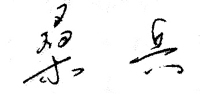
桑兵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年9月
编 後
《中國文化》明年開始就要交郵局發行了,還是每年兩期,春季號五月十五日出版,秋季號十月十五日出版,郵發代號為80-617,關愛《中國文化》的朋友不妨輾轉相告,需要者可直接向當地郵局訂閱。
本期不乏可讀之作。范曾先生的李可染百年誕辰祭,情深如海,心香如寄,筆運如椽。他視李可染和傅抱石為黄賓虹后不可有二的畫壇巨匠,說他們都達到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境地”。而比李之畫作為“無聲之《離騷》”,尤為賞藝衡人之創闢勝解。其論李之天賦、力學諸宿因則曰:“生而知之,先生所固有,且脱俗超常,未可比量;學而知之,先生所恃守,虹吸鯨飲,豈能輕忽;困而知之,先生之抱負,博大雄奇,空視古今,此中包含着謙遜和偉大。”天道、畫理、守恃、哲思,盡在其中了。李是范曾先生的受業恩師,文後所附《自度曲.懷可染師》之尾段悲懷跌宕,瞻夫來路:“我的悲懷彌六合,恩師已去典範樹。他舍依傍,駑鳥不群空今古;他瞻異代,春蘭秋蕙芳馨吐。魂魄猶在江山圖,嘯傲似聞空谷足,預留下驚鬼泣神的宫商譜。浩茫向天宇,一辦心香和泪書。”
前些時朱维錚先生寫過一篇題目叫《天下幾人能及君》的文章,評介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學術貢獻。《舊五代史》係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薛居正監修,一百五十卷,明代該書亡伕,後來的通行本是四庫館臣邵晋涵依據《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所重輯。邵輯使得二十四史逸而能全,固然功垂後世,但問題也不少,主要是誤收、錯簡、遺漏.所以陳援庵等史學大家一直主張應該重新輯錄校訂此書。如今這項工程由現年五十五歲的陳尚君完成了,歷時十一年,新輯紀、傳、志五十三,增列傳六十,删清人誤收九,改訂、乙正八干處,補逸文數萬,附錄五代實绿遺文百萬字,都三百二十萬言。這是他繼《全唐詩外編》、《全唐文補編》之后創造的又一史學奇迹。大家通過“文史新篇”裹的《<舊五代史>重輯的回顧與思考》一文,應可窺見陳尚君先生辛勤治史的心路歷程。
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論古籍十種,曰《周易正義》,曰《毛詩正義》,曰《左傳正義》,曰《史記會注考證》,曰《老子王弼注》,曰《列子張湛注》,曰《焦氏易林》,曰《楚辭洪興祖補注》,曰《太平廣記》,曰《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論老十九節,六十三頁,是《管》書的重要部分。時人研老多有牽引錢先生觀點者,獨乏系統論述。張隆溪先生的《錢鍾書論<老子>》,對此一義題作了迄今最全面的梳理,頗具參考價值。况隆溪擅西學,自多一與《管錐編》作者對話的根基。《論陳寅恪的闡釋學》是作者論陳專書的一章,最近經改訂重寫,給出新的框架,特别是“地域與家世信仰的熏習:闡釋的種子求證”一節,作者自覺不無新意,故刊此以待大方之家。
“名家述學”是新欄目,本刊闢此有典述家學傳統之微意。范曾和舒蕪兩位先生自是名家、大家,而其家學又堪稱淵源有自。范是南通范,宋名相范仲淹之族裔,明清以還十三世代代能詩,至范曾書畫兼擅,而尤以詩學能直承晚清詩壇巨擘范伯子的衣鉢遺緒,卓然成一大家。《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是他調入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后所作的第一次演講,為保留現場的氛圍,主持人的開場語一并附存。恰好范曾不久前有《炎黄賦》之作,二十年前他還寫過《莽神州賦》,為呼應家學專欄,我們征得作者同意,特連同書法一體披載,睹凌雲氣象,賞詞采華章。方是桐城方,但不是方苞一系的“大方”,而是方東樹一系的“小方”。但“小方”也是大家,直到舒蕪(方管)的尊人方孝岳,仍以文名聞世。舒蕪的外祖父是桐城派殿軍馬其昶。馬和范(當世)還同為桐城姚家的女婿。本期刊載的舒蕪先生緬懷母親的文章《平凡女性的尊嚴》,寫的正是馬其昶之女與方孝岳結儷而又婚變的“棄而不怨”的凄美故事。文是舊文,事是往事,但其情其境有足堪玩味者。
來新夏和李學勤兩碩學的文章同時刊於“古典新義”專欄,想必為讀者所樂見者。李文釋證楚簡《慎子》,遥想地下發掘物中所呈現的晚周諸子百家争鳴的景象,并追思不久前去世的英國學者譚普森(Paul Mulligan Thompson)研究《慎子》的著作與成就,言簡而意篤。來文則圍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皕宋樓藏書被捆載東渡歸日本静嘉堂文庫的歷史事件,對陸樹藩是否要負“未能善守家藏”的全責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特見。“文化與傳統”一欄内容亦豐,既有摩羅針對原罪情結、懺悔意識的宗教學分析,又有鄭誠、江曉原根據佛國曆術故事的流行和隱没,所作的文化學描述,更有胡曉真獨闢蹊徑,從城市感官經驗的審音辨色中,探訪江南名城杭州在歷史轉折中呈現的不同面貌。
“明清文化思潮”一组文章,從晚明走到晚清,從内政走到外交,從本土走到東瀛。劉志琴探討近代因素在明中葉以后的萌動,不妨說是老問題的新論述。而通過對《鄭孝胥日記》鈎沉排比,李振聲帶領我們重返晚清歷史現場,領略海藏樓主人未可“一言以蔽之”的多面性格。姚鼐自是桐城派的關鍵人物,卞孝萱等重新檢視《桐城麻溪姚氏宗譜》并征引相關資料,對姚氏的事功及鄉里家族背景勾沉索隱,多人所未發,且可與范、方述學成無形呼應之勢。
不過“現代文化現象”專欄的三篇文章,尤不能不向讀者介紹。陳方正先生比較論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雖為舊題却存新蕴,提出兩者不獨破壞性一面即建設性一面亦有相通之處,并追溯了兩者的思想資源及其來路。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楨日記》,涉及馬一浮的記載多有删節,學者引用常有頭尾不全之感。現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新版《竺可楨日記》,恢復了删却部分,因此更加珍貴。虞萬里先生就是以《竺可楨日記》為原料,爬梳一代大儒和一代科學家之間的因緣際會,於竺於馬不啻實錄。而《王國維全傳》的著者陳鴻祥先生,考訂王國维和吴昌綬的詞曲之緣,補虩虖漏,足為談資。
本期“文學的文化學闡釋”兩篇文章都是音樂性的。李思涯用酷似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叙事風格,做了一篇翻案文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漢武時期樂師李延年的這首“新聲變曲”的女主角,當病重將亡“形貌毁壞”之際,拒绝皇帝缘悭“一面”的懇請,既保持了皇帝心目中對她“平生容貌”的愛悦深情,又間接護佑了自己家族親人的功名富貴。從“一見”到“不見”,色衰而愛不弛。信夫,李夫人乃善以美貌為進退策略者也。因此這篇《漢書·李夫人傳》的“另一種讀法”,說不定還值得一看呢。同樣,李若暉解讀李商隱《錦瑟》詩的特殊視角也會引發我們“回到詩自身”的興趣.至於“無端”的“追憶”竟然華彩驚艷如此,是否已成“鄭箋”,只有知者知之了。
《中國文化》也可以刊載今人的文學作品,創刊伊始就有先例,汪曾祺、王安憶都留下過身影。本期“今人文存”收錄一篇文體試驗之詩性小說,雖後生少作,亦諸法平等,是耶非耶,讀者鑒之。
最后,我們對周策縱、龔育之兩位學術顧問的不幸仙逝,表示深切的追念與哀悼。周先生,二○○七年五月五日,逝於美國,終年九十有一。龔先生,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逝於北京,終年七十八歲。他們都是湖南人。周先生長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陌地生,通譯麥迪遜,周先生故意譯作陌地生,以寓對故國思念之微旨。
2007年9月l6日
文章分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