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各位网易网友光临网易泡泡聊天室,昨天晚上7:06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老人在上海逝世。今天我们请到了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与我们一起聊一聊巴金,首先我们请钱教授跟网友打个招呼。
钱理群:我是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
主持人:您认识巴金老人吗?
钱理群:我阅读中认识的,我们算是校友,我是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巴老是我们的学长。
主持人:您觉得巴金是什么样的老人?
钱理群:我们南师附中校园里有一个巴金塑像,题了个字:掏出心来。我对他最深的印象,他是很真诚的作家,他把心掏给了读者,我们能最亲切的交谈,巴金在我心中是非常亲切的形象。
网友问:您认为在现代中国史中间巴金先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钱理群: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作为人的巴金的精神,另外创作上的贡献,主要是长篇小说家,所以他对中国长篇小说比较突出的贡献。
主持人:哪些作品最能反映文学成就?
钱理群:一部是《家》,一部是《寒夜》。
主持人:巴金老人在解放后在小说创作上我的印象中没有深刻的作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钱理群:解放后影响最大的《团圆》,关于写会见彭德怀的文章,不仅在他身上发生。巴金老一代作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写,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49年之后,因为政权很大变化,他的对象都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些新的生活,所有老一代作家不能适应。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来写熟悉的,要求写新的人,新的时代这对他来说困难。在政权变动以后,很多作家还是很愿意为新中国写作,毕竟不是他最熟悉的。
主持人:各位网友也都知道,文革结束之后,巴金先生写下很多文字,收集到随想录里面,您怎么看待?
钱理群:《随想录》是巴金晚年一个作品,代表新的思想境界,我觉得巴金在这里表现非常可贵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一个精神,我觉得这应该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表现出巴金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首先正视历史,不仅正视历史本身的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遗愿恐怕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一个问题。
主持人:巴金先生曾经说,文革我们往往归结到四人帮,很少看到整个民族悲剧,巴金作为一个亲历者反思文革,似乎整个民族反思,或者发现文革中间所暴露出来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您是否认同?
钱理群:我觉得两个层面,一来文革发生有历史责任,所以我并不赞成文革过于强调普遍老百姓反思。因为文革是全民参加的,跟别的运动不一样,这是文革很可怕的方面,这样使得每个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间都有一些痛苦记忆。
主持人:巴金《随想录》里面说知识分子应该讲真话,年轻网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巴金先生提倡这个大家可能不能明白意义所在,我知道钱老师您在有一篇文章《说话底线》,一个做人应该说真话,第二个想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应该沉默,第三个不得不说假话,不能加害别人。这是学术届称颂的,您能不能介绍这里面的故事,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您的这段话?
钱理群:说真话是人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所以我今天上午接受一个记者问我,想从知识分子讲,首先知识分子是人,普通人应该做到事情,知识分子应该做到,讲真话既是人的底线,也是知识分子的底线,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应该作为民族时代精神一个体现者,所以他更应该说真话。我提供一个机会稍微阐述我这个观点怎么产生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实际上我曾经收到一个大学生来信,讲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必须对某件事情表态,他不想表态,但是必须表态,如果不能表态就不能毕业。我当时看着很痛苦,我也很困难。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说真话,应该拒绝,这就意味着这个学生不能毕业,我认为不道德的。他如果听了我的话,连工作都没有了,这个对我良心上过不去,我很坚持这样,别人觉得这个人说真话,使别人陷入困境。我原话是这样意思,人是应该说真话,这是大的前提,也是判断是非最基本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应该坚持说真话,特别情况下不允许你说真话,这个时候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沉默,保持不说假话。
实际上大学生给我写信所遇到这个情况,他遇到非说假话不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只好被迫说,实际上我想三条线,传说讲一条线,实际上我讲三条线。第一个分清是非,前提不是认为说假话是对的,是错的,有的时候必须做违心的事情。第二条底线必须是被迫的,不能是为了别的目的,是达到个人的目的,主动去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第三个,不能损害他人,即使你说的错话,谎话造成后果你自己承担,包括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更不能伤害别人。所以我讲的是包含了一个不要损害他人,同时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因为我研究鲁迅,受鲁迅影响,鲁迅一方面强调说真话,但是另一方面劝告年轻人赤膊上阵。他主张年轻人善于保护自己的。当这两者之间有统一,基本上统一的,但同时有一定矛盾,但具体怎么处理,怎么掌握度,这确实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就这么原则地说。
主持人:我们先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这里有一位叫做"斯基"的网友,他说家族文化对于形成中国普通民众的身份认同有很大作用,这里面甚至包含这一底层公共空间形成的可能性,钱先生怎么看待巴金对"家"的解构。
钱理群:实际上巴金对家的理解描绘实际上有变化,一个是《家》,家是写在三十年代,那么三十年代当时一个很中心的主题个性解放,觉得中国传统家庭,特别是封建家庭,那个《家》高老太爷绝对统治,封建专制一种性质的家庭,所以巴金控诉这个家庭,他走出这个家庭是这一代年轻人思想解放,走出第一步。五四以来当时年轻一代的选择。到了四十年代巴金写《寒夜》,面临外族侵略的情况,人们对家的理解有一个变化,就每一代人对这个家庭的认识,家族化的认识和描写是受环境影响,到四十年代巴金的家和三十年代家不大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出小说女主人公,想走出家庭,又回到家庭这样一个矛盾,而最后是她是又回来了,所以说明到四十年代对家庭更复杂的一个态度。其实你可以比较老舍《四世同堂》是国家的细胞,成为一个坚守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后人对前人的东西应该有一个理解。
网友张敏:请问钱教授怎么看待冰心和钱钟书。
钱理群:应该说他们文学上差别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巴金和冰心稍微接近一点,钱钟书更不同一些。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中国文学贡献,他们都是中国语言大师,冰心提供了她的散文,巴金提供了他那样充满青春气息流畅的白话文,钱钟书给我们提供了充满了幽默感,充满调侃,从语言上来说更加丰富。把外国,中国传统的语言口语有机结合起来,但他们三个文体又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巴金的文字相对来说是更多的白话文语言,冰心的文字更加柔和,很多文言的成分,而钱钟书是把外国的传统文言和白话有机结合,所以他们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都是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特别突出的是巴金和冰心,他们作品中充满了一种爱,大家看见钱钟书老是冷嘲热讽的,实际上内心深处也是人道主义者,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很可贵的传统。
主持人:怎么看待当代知识分子良知的问题。可能文革到市场经济,普通知识分子对良知看得特别重,把希望重责压在知识分子上,希望他们肩负起,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钱理群:其实我的观点,我觉得知识分子更应该是个普通人,所以我把巴金更看作一个普通人,所以我的文章里面讲说巴金是一个好人,一个可爱的人,一个有理想、信仰;一个真诚,一个很纯洁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看来对知识分子一个批评或者对知识分子失望了。我觉得当代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自我反省意识,一个缺少社会承担这样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期待,期待本身是一个失望,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另一方面不必要夸大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最主要还得靠自己救自己,靠每个中国人自己救自己。我对这个问题很悲观,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他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已经承担不起,所以成为我们怀念巴金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中国知识分子缺点是什么样子的?
钱理群: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面对几个危机,一个方面就是能不能够抵制体制的诱惑,经济的诱惑,还有你自己内心的某种欲望这种诱惑,那么这样一些诱惑,实际上都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巴金很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写那个文章讲到,面对巴金,我自己也算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羞愧难言。巴金有理想,有信仰的,我们确实是信仰缺失,巴金是真诚的,我们现在越来越不真诚的,巴金很单纯,我们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心灵被灰尘和油腻堵塞了。
主持人:刚才说到了理想,您认为巴金的理想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有一句话,巴金很朴素的理想,希望每个人都有饭吃,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书读,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房子住,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巴金一个理想,看起来很低,但是他强调每一个人,这个包含了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知识分子最喜欢讲自由,实际上巴金的观点,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不幸福,你就不能不幸福,世界上有一个没有书读,你就不能说有知识。我们当代中国现实,大家觉得巴金非常朴实的愿望,切中当下中国的要害。比如他对文学有个理解,他说文学使得变得更美好,我们还是给人越来越卑下,卑微,越来越肤浅呢?巴金为常识性的理想、信仰奋斗一辈子。他翻译一篇小说《燃烧的心》,巴金为他的理想燃烧了一百年。
主持人:您认为巴金老人离我们而去了,中国人里面谁能接替巴金所处的位置?
钱理群:我是研究现代文学,我对当代文学不是太关注,具体说出来某一个人可能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也不是绝对悲观的。一个火种不可能熄灭的,实际上也会有一些作家,继续坚持巴金面对现实,像巴金说真话,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主持人:巴金倡导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这与巴金先生实际的状况是不是相违背?
钱理群:这个说到了巴金的悲哀了,我今天正好带了一个材料,巴金晚年有一句话,他说我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也充满烦恼,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应付这些人,我痛苦不堪,偏偏人老了,来日不多,时间可贵,偏有人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巴金晚年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不幸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所谓名人很难避免的一个悲剧,我们理解鲁迅去世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叫"忘掉我",我想巴金大概也有这样一个愿望。一方面说明巴金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悲剧,如果想作为个人巴金来说,社会进步了,我们不必谈巴金了,他希望别人忘掉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作为一个现象来说,巴金晚年不由自主的,因为他不能说话了。
网友耗子:在今天的新华网的发展论坛里,网友"天父"写了篇"巴金到底是谁的良心?…",文章的大意是巴老在文革中在农村下放的委屈而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他本人从未为当前的劳工和农民处境说过一句话。有人说巴金是人民的良心,这让人很费解,您是怎样看待的?
钱理群:这位网友提出没有当下这些弱势群体说话,我想是指这样意思,我想这需要考虑一个背景。我一直反省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其中很大的失误,中国初期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的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发出声音来,而过于关注自己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一代人的问题,可能不应该是巴金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关注到弱势群体的问题,这个时候恐怕到了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所以大家比较多弱势群体的时候,巴金已经很老了,已经重病缠身了,不再可能说话了,所以我觉得应该理解老人,我觉得不能苛求这个老人。这里也有他的困难,比如说你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能做具体的事情,如果不能做,口头上同情他们,我觉得反而没有意义,我想巴金不说也可能什么原因?空洞表示同情没有很实际的意义,也是我们感到困惑一个方面。应该说这几年历史有些进步,我想这个情况也在改变,对老人有一个理解,不要太苛求。
主持人:巴金85年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巴金的选集里并没有把文革博物馆这个说法放进去,您怎么看待?
钱理群: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这里就是他同时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像巴金,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生中不断做出各种妥协,如果这个事情像网友说的情况下,可能也是属于巴金所说的妥协,当然现在无法做具体解释,但想强调我们类似的经历,我自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把一些话删掉了,或者同意别人把这句话删掉了。什么原因呢?你这本书出来以后,出了问题之后,不惩罚作者,惩罚出版社,所以你为出版社着想,不得不做妥协,自己说话自己责任,但如果说自己不承担责任,相反别人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时候有犹豫,经常考虑别人,同意原因很简单,不是为我,不是我的问题,端了别人饭碗了。像知识分子做这样的妥协,也需要要理解具体的环节,具体情况我不太理解。
主持人:说话底线不要伤害别人,您刚才说过真话对第三方造成伤害。
钱理群:不是,我们受体制的干预,但是因为有这句话,这个书不能出来,这个出版社受到什么压力,只能够做一种妥协,实际上鲁迅他说过,现代读者很难看见很有骨气的文章,什么原因?国民党检查制度,我作者写文章抽掉几根骨头,我在这里讲话,我的话说不定抽一点骨头,否则说不定造成什么后果,然后编辑抽点骨头,主编抽点骨头,最后读者看到东西没多少骨头,鲁迅说的三十年代的情况,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有一个理解。
网友Guest2说:钱老师好,李敖刚刚离开北京,他在北大演讲时,讲到公民和政府有以下几种关系,一种是死掉,一种是逃跑,一种隐士,一种是硬斗,他本人觉得用很技艺的方式去争取自由。您怎么看对自由的争取方式?方式是不是决定了结果的性质?
钱理群:李敖的讲话没有完全看,但是我听说李敖,打过一个比方是关于争取自由的,要像女人撒娇那样争取,如果这样讲,我是不同意的。如果像女人撒娇争取自由,绝对不叫争取自由。我刚才说到妥协,有的时候不可避免,但是妥协有个度,有些不能妥协的,或者有些方式不能采取的,就是要有度,我们不能没有妥协,但是这个妥协必须有个度,包括妥协的方式,如果李敖说像女人撒娇争取自由,我绝对反对,但是这个当中是不是采取策略,这是第二层面的问题。第三这个策略要有原则,违背原则的策略,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网友耗子:提到说真话,讲实话,巴金说过哪些真话?哪些真话最能够打动您?
钱理群:巴老因为某种程度说的,但是我们年龄差距很大,巴老的经历我们共同经历过来的,巴老讲到"在中国这种思想改造的可怕,就是思想改造可怕在哪里呢?不管别人怎么改造你,就是自己来否定自己,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那么我原来看过他的话,最受震动这一点,我自己有类似的东西,不完全在外在,是自己内心觉得自己是应该改造的,自己是可耻的,对于人的精神控制,我觉得巴金对专制体制对人精神控制揭露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真实的。
梁京午后的咖啡说:现在大家都会质疑知识分子有没有资格拯救他人,比如弱势群体,巴金虽然主张说真话,也不能成为一个拯救者,人人自救不过是一个梦想乌托邦,我想问老师的是巴金能否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无力而执着。
钱理群:对,我同意这个网友,这个网友分析很到位的。我们不必巴金理想化,不要典范化,我这个文章里面曾经有一个说法,不要把巴金抽象化、历史化,把作为人的巴金剥离了,他是知识分子中一种方式,无力,但是执着,巴金绝对无力,有再多的巴金拯救不了中国,但是他执着,另外一个意思说贯穿中国传统精神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巴金很清楚他自己,但是他认准的事情必须去做。实际上知识分子非常无力的,外在体制无力,内在也是无力的。但是巴金执着,其实体现这样一个精神。巴金就是一个过程,这个网友说心灵的过程,代表这样一个历史。他对于我们只是一个启发,我们不会把他当榜样,不会当典范,对我们是一个启示,更主要我们自己怎么面对现实,我们自己怎么做人活着。
主持人:巴老对现代青年作家有什么告诫?
钱理群:我不知道他对现代青年作家有什么期望,但我知道不断对他朋友提出这种期待,你们是作家不断写,不断把自己心里好东西写出来,不断劝他的同辈,某种程度上对年轻作家一个期待,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
主持人:钱老,您原来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您怎么看待大家对北大的看法?可能原来年轻人看北大是很崇敬,很敬仰的目光,现在大家观念发生一些转变,这些转变是北大的不好。
钱理群:那时候没有退休的时候,有同学经常向往来北大,来找我的时候,我先给他们说一句话,别把北大理想化,北大不是你们想象一个梦乡。我说你们牢牢记住一点北大是中国的北大,中国所有的问题北大都有。后来人们老是讲北大,所以我多少修正我的看法,虽然这些年轻人向往北大是一个梦,但是我觉得一个民族总是有一些地方让年轻人做梦,如果一个民族连年轻人做梦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个太可悲了。所以现在人们对北大看法的转变,我想做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评价就是说他们更接近真实的北大,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点悲哀,本来可以做梦的地方,这个梦都没有,就是我的观点。不仅是北大的悲哀,而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悲哀,现在年轻人想做梦,一个一个梦破灭了。
主持人:巴老的"十年一梦"有一个序言,而是我知道一切梦…是不是反映一种心态?
钱理群:梦醒的时候是失望的,梦醒是一个好事,特别是年轻人不做梦也是一个悲剧,也是不正常的。
guest2说: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和胡风已有20年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写下批胡檄文。当人们为鲁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风是特务,巴金奋起反驳: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骗!最后一根可能救胡风命的稻草就这样被巴金给掐断了。钱老师能谈谈胡风事件中的巴金心态么?
钱理群:因为我不是研究巴金传记的专家,我对具体的不是很了解,我可以算是同一代人。虽然我们那时候经常遇到一个矛盾。我讲我自己经历,苏反运动的时候,学校批判我一个很好的老师,当时党支部找我谈话,希望你批判老师会上发言,当时我很痛苦,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当时摆两个东西放在我面前,一个是我老师是我的恩师,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党,我们这一代人形成一个观念,党总是对的,那么最后听谁的?而我们最后听了党的,听党理由就是说,也许党是最全面的,也许老师还有方面我们不知道的。我想巴金多少面对这样一个矛盾,一个很熟悉的胡峰,另一方面是一个党,为什么巴金研讨,为什么反省自己。党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果有错疑就是个人,而不是党,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党被神圣化以后,任何和党矛盾的话,错的肯定是那个人,即使我很熟悉,即使我很了解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
网友曲终人散说:"我有思想必须倾诉,我有感情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巴老的这话我一直记得很深刻。不知道钱老师说的不要把巴金做典范,做榜样,那么我们要什么样的榜样?
钱理群: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巴金当一个倾诉者,倾听你的倾诉,其实不仅巴金,其实我的职业任务之一不断倾听年轻人各种倾诉,年轻人需要有做梦的地方,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地方,这样有经验的老人应该扮演这个角色。实际上我觉得与其把巴金作为一个典范,不如把巴金当做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忘年交,这是一个可以向他倾诉的朋友,因为他的人生走得比你长,他很有经验,他的这些东西作为你的参考,他可以对你有所启发,有所提示,你有问题也可以请教,我想作为这样一个对象,这样关系可能更好一些。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巴老一些思想还有知识分子一些问题,作为文学家巴金钱老您怎么看?文学上的意义并不具有多大的价值,您怎么看?
钱理群: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就是说巴金贡献两个方面,一个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应该算是历史的贡献,另外他语言的贡献,就是巴金创造了一种。巴金创作青春型的文学,而且包括他的语言,倾诉性的语言。我们客观说巴金也有自己的评价,他的朋友中最有文学创作才华是曹禺和徐志摩,他没说他的自己,我也同意他自己,就文学才华而言,巴金并不是最突出的,所以在我看来比起曹禺,比起徐志摩可能要差一些。这个当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文学成就,至少巴金很重要的作家,到底是什么位置,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巴金是属于非常真诚,非常勤奋的,非常执着的,巴金不是才智型的作家。
午后的咖啡说:知识分子必须有政治担当的能力,现在的知识者比如大学生已经很少有这种意识了,我们所困饶和被支配的是一己的生活满足,现实的压力把你紧紧闭塞到生活的柴米油烟中,成为一种市侩主义。钱老师曾经对于大学教育表示过忧虑和批评,您对大学生这种缺少政治担当的境况怎么看?
钱理群:我觉得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知识分子有社会承担的,这个承担包括政治、道德,所以仅仅提政治承担不是非常全面的,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大学生和我们不大一样。我一直和学生说,学生处在一个准备阶段,我开玩笑跟大学生说,你们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幸福的阶段。比起中学生,有公民权利,但是没有公民义务的一个阶段。因为你是准备阶段,还是不到为社会服务的阶段,基本上没有社会义务的阶段,大学生总体来说应该为社会长远发展做准备的阶段,而不是为社会服务承担什么的时候。当成年人搞不好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出来,总体来说在学生阶段,我觉得不是承担阶段,既然你是一个准备阶段,决定你将来的发展。我也跟大学生们说,做学生阶段首先保证你的温饱,但是我觉得在大学期间主要精力还不是赚钱,这个还是应该集中学习,基本生存前提保证下,主要提高文化修养,我的忧虑是大学被过多物质欲望所纠缠,这是缺乏远见的。我们不是反对功利,要有长远的功利,不要追求眼下的功利。小而言之,涉及到个人发展,大而言之涉及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
网友耗子说:晚年的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的愿望。一个敢于直接面对精神的苦难,敢于鲜血淋漓的解剖自我,把丑陋和赤裸身躯展示给读者的老人,他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生死、面对人生最后岁月的痛苦吗?
钱理群:巴金说别人要我做不愿意的事情,到最后什么不能做。他讲人生观,我活下去是为了给予,而不是为了索取,到了最后他已经不能再给社会什么了,能给的都给了,到最后确实不能给什么了,这个时候再活下去了,只能取了,造成这个社会的负担,所以他觉得我该离去了。实际上很多老人都有这种心理,燃烧一辈子,燃烧尽了,活着确实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所以他觉得自己该离去了,这某种意义上倒不是回避生死,反而敢于面对这样一个死亡精神,而且他对于生的理解是很深刻的,生是给,不是取,他这样一个生命观来使他愿意安乐死。
主持人:钱老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巴老也是您研究的对象,昨天巴老与世长辞了,因为您也说到了您跟巴老现实中间没有具体接触过,如果您要对巴老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想巴老说的话,巴老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可爱的人,那么你一路走好。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现场的网友对于这次访谈反应很热烈,不断有网友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此次访谈到这里只能是告一段落了,期望在下一次的访谈里,欢迎各位网友再次光临网易的聊天室,与我们一起和嘉宾交流,谢谢诸位网友,谢谢钱老师,再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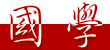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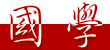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