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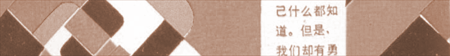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
|
|
公元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
|
|
|
|
|
|
|
||
|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 而《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写曹操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实际上就是英雄之名目的具体商榷与研讨,生动地反映了建安时期的论人风尚。《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附《陈登传》: 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辛弃疾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全宋词》,页1869)说的就是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当时士人推重抱负远大的英雄,故汲汲于小利如许汜者,特别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薄。其实,这个名目在两晋时代余波犹存。《裴启语林》六九: 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潘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 又《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庾翼)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潘岳、石崇是西晋名士,而庾翼和桓温是东晋名流,足见此名目流传之久远。而这个名目,在南朝被文学理论家所吸纳,成为文学评论的一个常用语词。我们看《文心雕龙·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搆。”“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及读钟嵘《诗品·总论》:“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陈延杰《诗品注》,页2)“季伦(石崇)、颜远(曹摅),并有英篇”(同上,页36),“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 同上,页71),均可发现原本属于人物品藻范畴的“英雄”之名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由此可见人物品藻对中古文化影响之一斑。 本书上篇试图展示人物品藻的各个方面,重点澄清与此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古时代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关于清谈所涉及的各种哲学问题,冯友兰、侯外庐与贺昌群诸先生都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近人的著述也颇为可观(参见本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这对我们认识清谈的文化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对于清谈内容的具体问题不妨各抒己见的话,那么,关于清谈形式方面的问题则急需得到确实的阐释,因为目前在这方面尚有许多混淆不清的地方。对于中古清谈的某些基本问题,我本人关注了许多年,也困惑了许多年。1988年,我读了王葆玹先生的《正始玄学》,真如拨云见日一般,许多与清谈有关的问题都了然于心了。这确是一部材料丰富、新见叠出的学术力作。然而,由于此书以关于正始玄学问题之研讨为主,而非探讨清谈问题的专书,所以在叹服之余,尚觉未惬我心。大约在1994年7月间,我见到唐异明先生所撰《魏晋清谈》一书。此书旁征博引,几乎将与魏晋清谈有关的学术资料一网打尽,同时加以细致、严密而准确的科学分析,于是清谈问题的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都毕现无遗,昭然若揭了。此书在清谈的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之作,书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视为定论。在该书的《绪言》中,唐先生指出: 一九四六年,又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也题为《清谈》的文章。……他把魏晋名士分为清谈派与清议派两种,又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二四0~二四九)、白银时代(七贤,二五0~二六四)、西晋(二六五~三一六,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代他称为黄铜时代)、东晋(三一七~四二0,马瑞志代他称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魏晋清谈》,页9) 马瑞志先生在其著名的英译本《世说新语》的导论《<世说新语>的世界》中,也复述了宫崎市定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他们的说法。在本篇中,我对清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形式方面的问题,而不以其思想内容为第一着眼点。我试图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谈形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的研讨,来考查清谈的某些本质特征。 当然,就清谈的研究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材料还是《世说新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页194。余英时先生说:“《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语》所收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尤大于其下限也。”见《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307页。子烨案:此说极为精彩,余深然之。唯“《世语》”,疑当作“《世说》”,以晋人郭颁之《魏晋世语》通常称为《世语》,故于《世说新语》不当以《世语》为称也)《世说新语》是清谈名士的“教科书”,其妙言隽语,精理玄旨,无不毕见于此书。作为清谈之书,它实际上也就是清谈家的语录。所以本篇对清谈的研究,主要取材于《世说新语》,同时参考魏晋南北朝各朝正史的有关记载。 本书下篇包括四篇专论。在这四篇专论里,我分别探讨了与中古文人生活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我的着眼点在于中古文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在种种“原生态”中所浸透的文化观念。因此,本篇之所言,就不仅仅局限于生活的本身,而是着重阐发生活主体的意识形态。我试图通过对中古文人个体生活的述描,展示其群体的文化走向。换言之,在士族文化的浩淼烟波中,我们不但要窥察其中的每一片风帆,而且还要追随它们所组成的声势浩大的船队。当然,中古文人生活的具体显现也是多姿多彩的,这里所撷取的也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