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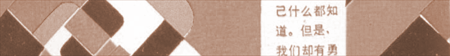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
|
|
公元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
|
|
|
|
|
|
|
||
|
二、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习俗 (二)挽歌盛行的文化背景 中古时代是富于艺术情味的时代。就艺术本身而言,弥盖朗琪罗所谓“修炼艺术的,当是贵族而非平民”(罗曼罗兰《弥盖郎琪罗传》,《傅雷译文集》,第11册,页160)的说法并不能完全成立,但我国中古时代的艺术完全操持于贵族之手则是事实。不仅如此,彼时的艺术还由于贵族的修炼而达到辉煌,而音乐艺术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三国至两晋的乐坛,名家如云,音乐也成为世族豪门的家学(参见本书页211)。贵族们欣赏音乐,尤其偏重于悲哀的情调、凄美的风格,或者催人泪下、令人销魂的韵味。上文我们引《世说新语·言语》六二,王羲之对谢安说丝竹之音足以倾泻其“伤于哀乐”的情怀。又《晋书》卷八一《桓宣传》附《桓伊传》: ……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桓伊所歌《怨诗》,为曹子建所作,逯钦立《全魏诗》卷六题作“《怨歌行》”,且于“二叔反流言”句下有“待罪居东国”等十四句。《晋书》卷二三《乐志下》著录晋鼙鼓歌诗五篇,其中《明君篇》之下题曰:“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此魏曲当即曹子建《怨歌行》,乃系曹魏宫廷旧曲。在士族艺术家看来,音乐之美在于传达人类普遍具有的悲绪哀情,音乐艺术的不朽魅力在于其深蕴、缠绵的悲美。如果说孔子“诗可以怨”的诗学观和以屈宋为代表的南楚悲怨文学为这一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中古时代的挽歌则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与挽歌同步,上承先秦悲怨文学之传统,从东汉末年以迄六朝,哀怨之作在文人五言诗和抒情小赋中大量衍生,贯穿于其中的以悲为美的观念在梁代钟嵘的《诗品》中得到了明确、深刻的理论总结。钟氏在《诗品·总论》中指出: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诗品注》,页2) 一个“怨”字,虽然难以囊括中古诗歌之特色,但挽歌之特点则可以由此而毕现无遗。挽歌之“怨”是哀怨,是悲怨,可以说,以悲为美的观念被它发挥到了极致。 挽歌之风的盛行也与士人的人生哲学有密切关系。《庄子·齐物论》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觞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然如此,在悲与乐、祸与福之间,便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妻子死了,庄子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而魏晋士林悠扬的挽歌不正是庄周式的人生观的富于艺术美的外化么?上文我们引用了《世说新语》这部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中的几个关于挽歌的故事,它们被站在礼法之士立场上的作者编入《任诞》篇,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士林放达之风的鄙斥,更说明唱挽歌之举有悖于传统的儒学礼仪观念,特别是《礼记·檀弓上》所说的“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魏晋之际,儒学与道学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由此可见一斑。但彼时老庄学说毕竟日丽中天,因而挽歌不断深入人心,与宫庭廊庙的雅乐并行无碍。士人们留恋生,所以就更加关注死。生、死情结的矛盾,成为中古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之,与艺术家们凄迷的歌声相伴,挽歌诗在诗人的笔下不断涌现。
|
国学网站,版权专有;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