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略说《金刚经》论注之历史沿革
帝王之推波助澜
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人们信佛,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风俗的┅┅就此而言,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他要想凭借政治的力量消灭佛教,那只能是一种至多得逞於一时、得逞於表面的倒行逆施,从古代的「三武一宗」之教难,到当代的「文革」,都是明证。但反过来,若佛教要真正地兴旺,则当局的支持,正确的政策,直至统治者本人的信奉,则是不可少的前提。弥天释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此之谓也。
《金刚经》之在中国广为传播,历代帝王之护持推动,实为一有力之增上缘。流通的《金刚经》六种译本,五本在帝王的直接护持下译出,一本则由地方郡守为护法而诞生,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一)前秦苻坚、後秦姚兴之於罗什译本
自司马氏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建立晋朝,四传五十年後,国势渐弱,以至接下去的十代一百年中,东晋王朝,只能偏安南方;而北方诸胡则先後立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其中苻、姚二氏,相继以「秦」为国号,为区别第一个统一中国之嬴秦,分别称彼为「前秦」、「苻秦」和「後秦」、「姚秦」。
史传鸠摩罗什入华以前,己经「道流西域,名被东国」。前秦苻坚建元十五年(379)沙门僧纯、昙充等自龟兹还,於苻坚前夸道∶「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同年,僧界领袖道安入长安,亦数度劝苻坚网罗人才,揽罗什入华。由此因缘,遂有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统领雄兵七万西伐之事,据《僧传》,苻坚为吕光於建章宫饯行时,特地关照∶
「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後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
但苻坚却与罗什无缘,吕光於晋太元九年(384)破龟兹,第二年苻坚即被杀,吕光得据凉州为王。吕光一介武夫,更非敬奉佛徒者,故罗什羁留凉州前後一十七年,未能宏道。
直至弘治三年(401),後秦国主姚兴(366-416)破凉州,迎罗什入长安,罗什法席,方始大盛。按魏晋之时,南北朝的帝王,信佛者甚众。相比之下,南方诸君,精通佛理者较多,如宋文帝、梁武父子、齐竟陵王萧子良等;而北方则唯姚兴一人,尚通佛法。然鸠摩罗什偏偏从西域入华,姚兴以国师之礼,为罗什置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场,一时俊杰,俱会一堂。天假其人,《金刚经》之鸠译本,遂以姚兴为大护法,得以问世。
(二)元魏宣武帝之於流支译本
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北方,初都恒安,後迁洛阳,再迁邺(今河南安阳北),凡十三帝,一百五十五年。史称「後魏」(区别於三国曹魏)、「元魏」(拓跋氏後改姓元)。
元魏自献文帝起,历代君王皆笃信佛教。浸淫日久,至宣武帝元恪时,朝廷上下,已信佛成风。宣武帝本人,常於禁中亲讲经论,并广集名僧,标明义旨。宣武帝灵皇后胡氏(史称胡太后者是也),造永宁大寺,据《僧传》描写∶
「在宫前阊阖门南御道之东。中有九层浮图,架木为之,举高九十馀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出地千尺,去台百里,已遥见之。初营基日掘至黄泉,获金像三十二躯,太后以为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饰制瑰奇,穷世华美。刹表置金宝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盘一十一重。铁锁角张,盘及锁上皆有金铎,如一石瓮。九级诸角皆悬大铎,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闲,六窗三户,皆朱漆扉扇,垂诸金铃,层有五千四百枚,复施金铎铺首。佛事精妙,殚土木之功。绣柱金铺,惊骇心目。高风永夜,铃铎和鸣。铿锵之音,闻十馀里。北有正殿,形拟太极,中诸像设金玉绣作,工巧绮丽,冠绝当世。僧房周接,千有馀闲。台观星罗,参差闲出。雕饰朱紫,缋以丹青。栝柏桢松异草丛集,院墙周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门,楼开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馀尺,状若天门。赫奕华丽,挟门列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玉,庄严焕烂。东西两门,例皆如此。」
以至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赞叹不已--
「永宁寺,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所立也┅┅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精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魏杨 之《洛阳伽蓝记》】
这样一座宏伟庄丽、举世无双的大寺,谁人有福驻锡住持呢?不是别人,正是《金刚经》之第二个译主--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汉名觉希,北天竺人。 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弘法,广流视听。以魏永平之岁(508倾)至洛阳。宣武下敕,殷勤敬劳,处之永宁大寺。当时永宁寺中供有七百梵僧,敕以流支为译经元匠。
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宣武帝对译经事业,非常之热心认真!
当流支创翻《十地经论》时,宣武亲自笔受,然後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僧传》赞曰∶「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
又,继菩提流支之後,天竺大德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相继入魏--
「帝以宏法之盛,略叙曲烦。敕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闲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後人合之共成通部。」
正因宣武帝如此护持,菩提流支能全心译经,始从洛阳宣武帝永平元年,终至邺都孝靖帝天平二年,前後近三十年。所出经论,共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菩提流支成为北道地论师之祖,而其所译之《金刚经》,也流传百世。
(三)陈梁安太守王方奢之於真谛译本
真谛三藏,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梵名拘那罗陀,或波罗末陀,译云真谛。法师之学,为世亲之嫡传。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 经论来华,初达南海(今广州),二年後(武帝太清二年秋)到梁都建业(今南京)。「佛心天子」梁武帝躬申顶礼,供奉於宝云殿,准备设立译场,传译经典。可惜时运不济,第二年即遇侯景之乱,武帝仙逝,真谛也开始了数十年的漂泊生涯。
据日人宇井伯寿之《真谛传研究》,近人苏公望《真谛翻译及事迹考》,梁太清三年(549)至陈大建元年(569),真谛三藏自五十二岁到七十一岁,整整二十二年,一直在南方流离∶
梁太清三年(549)--自建业入东土,後到富春。
梁大宝三年(552)--还建业,住金陵正观寺。
梁承圣三年(554)--去九江;再至豫章(今南昌),住宝田寺;又往新吴美业寺;继而再迁始兴(今广东韶关西)。
陈永定三年(559)--数年间,三藏在豫章、始兴、南康(今江西赣州西)、临川等处,「随方翻译,栖遑靡托」(《僧传》语)。最後停南越(即晋安),准备去 伽修国。
陈天嘉二年(561)--泛小舶至梁安,欲返西国。梁安太守王方奢为造建造寺,请留。
陈天嘉三年(562)--泛舟西行,欲返天竺,却因风飘抵广州。广州刺史欧阳 、欧阳纥父子,奉请三藏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延请三藏住於制旨寺。真谛见西归无望,遂於广州译经,直至往生。
可以想象,以三藏之高龄,恰遇中国南方变乱,於异国他乡流离转徙,其心情是何等的郁抑!所以法师屡欲西归,当西返无望,几至於自杀!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续高僧传》)
如此艰难的飘流生活中,真谛三藏终於挺过来了!他来华时所携贝叶梵本二百四十夹,居然译出了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这与无数信徒的支持及弟子们的追随,是分不开的。而《金刚经》的译出,梁安太守王方奢之护持,实是一大助缘!
在真谛经历多年的栖遑飘泊,无心暂留,下定决心要浮海西返之时,是梁安太守及时挽留了大师--太守特地为真谛造建造寺,其心不可谓不诚!或是天意,三藏最得意的弟子慧恺,也是在梁安首次参与译经。因缘俱会,因王方奢之请,六十四岁高龄的真谛三藏,於五月初一在建造寺,「依婆薮(世亲)释论」,重译《金刚经》,至九月二十五讫,《金刚经》真谛译本由此功德圆满。
(四)隋文帝、炀帝之於笈多译本
在中国历史上,有二个朝代,寿命极短,但对历史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一个是秦,虽说二世而灭,但「汉承秦制」,汉朝四百年天下,乃是秦制奠其基。几同於秦,隋也仅二世三十八年,但凡官制,政区,科举等等,大唐三百年天下,也是隋制开其端。至於佛法,唐之八宗俱盛,实与隋之兴佛,息息相关。
隋文帝杨坚,早年为尼智仙(仙)养育, 基後常谓臣曰∶「我兴由佛法。」故有隋一代,佞佛之风,远非前朝可比。除了大规模的立寺造(舍利)塔,度僧写经之外(《法苑珠林》、《历代三宝记》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号称「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文帝开皇二年(582)迁都龙首原,名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改遵善寺为大兴善寺,广揽名僧,制同太庙。文帝之大兴善寺,炀帝之上林园,乃是长安自罗什後,洛阳自流支後的二大译场,隋代佛法之盛,可想而知。
对於僧才之搜罗,隋帝更是不遗馀力,开皇七年(587)文帝召六大德入关;开皇十七年(597)敕立五众主,同年又敕立二十五众主;晋王(即炀帝)入洛,随驾大德数以十计┅┅经多年孜孜不倦「聚远方之英华」(《续高僧传》语),活耀於当时的大德,如三论宗之兴皇法朗、茅山大明法师、智矩;地论师之昙衍、昙迁、灵裕;禅宗之慧可、僧璨;净土宗之净影慧远;天台宗之慧思、智 、智锴;华严宗之吉藏;三阶教之信行;译经沙门彦琮、学士费长房;律师灵藏,智文;以及外国沙门达摩般若、那连提黎耶舍、 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全都是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开创性人物。
除了西域沙门之外,新罗僧圆光来游长安,旋即为其国主请回宏法;日本使臣小野妹子则奉圣德太子之遗,前来学佛。更有甚者,仁寿二年(602),天竺王舍城沙门前来长安,欲靖《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文帝敕令彦琮翻为梵文,合成十卷;盖译汉为梵,实为前所未有之事!
笈多三藏之入华,躬逢其时,躬逢其人,彼之於中土,实有深缘!
按达摩笈多,本南天竺罗棉国人也,刹帝利种,姓虎氏。年二十三岁,往中天竺耳出城黄华色伽蓝出家。二十五岁,方受具戒。受具之後, 历西域大小乘国,闻说大支那国,三宝兴盛,遂结契来华。经多年跋涉,於开皇十年(590),到达瓜州。据史载∶
「初契同徒,或留或没,独顾单影,悲喜交集。寻蒙帝旨,延入京师。处之名寺,供给丰沃。」【《续高僧传.笈多本传》】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国僧人,独自一人来到中国,举目无亲之时,居然马上就为中国皇帝请入长安,住进大兴善寺,参予译事--一是他本人确有才华;二是隋帝揽才宏法的大心和一套完整的制度;三是机遇;於笈多,此三者俱备--从此以後,先住长安大兴善寺,後移洛阳上林园;先是协助 那崛多,後是与彦琮一起主持译场,十九年间,二处其译经典四十馀部,《金刚经》即是其一。
笈多译本,乃梵文直译,与汉语之语法词序,颇不相同。据彦琮<笈多传>云∶「初笈多《翻金刚断割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及《普乐经》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史载彦琮於大兴善寺和上林园二处译场,主持多年,彼人精通梵汉,故於译事「再审覆勘,整理文义」,最後的精加工皆经其手。据此,所谓「未及练覆」、「不暇重修」,乃是彦琮没能最後润色。真是可惜!若非隋末天下大乱,我们今天或能看见流畅通顺的笈多译本了。
(五)唐太宗之於玄奘译本
唐太宗早年并不信佛,虽然他於开国转战中,屡为阵亡将士建寺立塔;讨王世充时,曾用少林寺僧兵;更於武德九年(626)反对高祖意欲沙汰僧尼之举;但这些都属政治措施,并非信仰使之然。就政治立场全体而言,太宗绝对是以儒家正统治国,且视梁武、简文为反面教员,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
「朕以无明於元首,期托德於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 。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徵,何其谬也。」【《旧唐书》】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
即使是从属於政治的宗教政策,他也因姓李而自称老子後裔,将佛教排在道教之後。其贞观十一年(636)诏曰∶
「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自今以後,斋供行立至於讲论,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於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集今古佛道论衡》】
贞观十九年(645)春,玄奘大师载誉从印度归来,太宗虽是征辽前夜,但也从百忙中抽出空来接见,从卯时谈到酉时,意猷未尽,还令玄奘随驾同行--然太宗的注意力,还是在政治(外交和了介西域印度的风土人情);所以当玄奘「固辞疾苦,兼陈翻译」时,太宗顾左右而言他,推辞再三,最後因玄奘固请,拉不下面子,才答应於弘福寺置译场。
但当太宗征辽归来,自感力气不如往昔,老之将至,遂有 生之虑,於是对佛教的态度渐渐转变,与玄奘的关系也日益密切,《金刚经》之翻译,就是即此因缘而成。
据玄奘弟子窥基大师述∶
「贞观二十三年,三藏随驾玉华,先帝乖和,频崇功德。共藏译论,遍度五人,更问良因,藏令弘赞,遂制般若之序,名<三藏圣教序>。其时太子亦制显扬论序。当许杂翻经论,并赞幽灵,既有违和,不暇广制也。于时帝问藏云∶『更有何善而可修耶?』藏报云∶『可执笔以缀般若。』帝既许之,藏便译出,其夜五更三点翻译即了。帝索读之,即遣所司写一万本。既不重缀,词句遂 ,後欲重译,无由改采前布也。」【19】《金刚般若经赞述》
唐太宗已一改往昔,度僧译经、「频崇功德」,亲制<圣教序>之馀,还请玄奘临时赶译《金刚经》,一夜而成,即写一万本弘布,真是因缘不可思议!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窥基所说的译本,乃是所谓「杜行 广本」,而现在一般流传的玄奘译《金刚经》,则是从大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九会,第五百七十七卷)中辑出。但无论何本,其译出均与唐太宗有直接关系。
(六)则天帝之於义净译本
武则天之称帝,佛教乃是其一有力之外援、舆论工具(从《大云经》称则天是弥勒下生,到《宝雨经》辩「菩萨杀害父母」,耳熟能详,不再赘言);故天后在位,大兴佛事,理所当然。至於则天帝於佛法流传,功焉过焉,史家自有论说;然义净三藏之译经,得天后大力护持,则是事实。
义净三藏,生於河南范阳(今涿州),俗姓张,字文明。龆龀之年(十八岁,一说十五岁),辞亲出家,史载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有志西游,未能谐愿。暨登具之後,誓期必往。」至咸享二年(671),义净三十七岁,壮志始酬,自广州经水路到天竺,前後二十五年,历三十馀国。於天后证圣元年(695)夏,携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金刚座真容一铺,并舍利三百粒,回到中国。洛阳缁素,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武则天亲迎於上东门外,旋敕於佛授记寺安置所 梵本,并令翻译。
初,义净三藏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久视年後,方自翻译自己带来的经典。从天后久视元年(700),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二年间,先後於福先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处,译出经律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馀卷。於是就有了《金刚经》第六种流通译本。
安史之乱之後,大唐帝国日渐式微;而後勿勿千年,或是外族入主(元、清),或是理学当道(宋、明),《金刚经》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译本。虽说因缘复杂,但除了没有国师级的译经大师之外,缺乏帝王之护持,不能不说是一原因。
返
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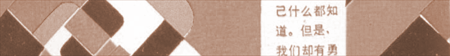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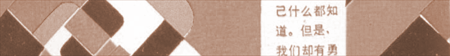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2896
010-62912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