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金刚经》二周说
如同很多佛经一样,《金刚经》是通过对话形式来弘扬佛理。而领出该经正宗分的,乃是须菩提(又译善实、善现)之发问∶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是鸠译,其馀诸译皆多一『云何修行』。)」
但只要稍微仔细读过《金刚经》的人,都会发现,同样的问题,须菩提问了二次。若以三十二分法言,则在第二「善现启请分」先问了一次;後於第十七「究竟无我分」又问了第二次;这就是所谓的《金刚经》二周。
或许有人会说∶前後重复,此乃佛经通例,有什麽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错,佛经是往往前後重复,如《大般若经》就有「两番嘱累」(《大智度论》说∶「先嘱累者,为说般若波罗蜜体竟;今以说令众生得是般若方便,竟嘱累。」)。但问题在於,一般佛经的重复,大都是先长行,後偈语,先说後唱;而《金刚经》不是如此,《金刚经》没有重述经义的偈语。更重要的是,经高僧大德、文人学者悉心探究--《金刚经》之二周,绝不是简单的重复!通过了解此二周之联系与区别;为什麽佛祖要不厌其烦,一说再说;前周为何而立,後周为何而设┅┅则能真正把握《金刚经》之精髓神魂,这就是所谓的《金刚经》二周说。
二周说的核心内容、根本精神,早在古印度己经被揭橥。无著所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於第二问处,作此论曰∶
「经言『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发菩提心住修行』等,何故复发起此初时问也?将入证道菩萨,自见得胜处,作是念∶我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心,我灭度众生,为对治此故,须菩提问∶『当於彼时,如所应住,如所修行,如所应降伏心』,及世尊答『当生如是心』等。
又经言『须菩提!若菩萨有众生』等者,为显我执取,或随眠故。若言我正行菩萨乘,此为我取,对治彼故。经言『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1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很清楚,无著菩萨注意到「何故复发起此初时问也」,他解释道∶是为了「对治」此种「随眠」(烦恼)--「我执」、「我取」,所以佛祖强调「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简单地说,《金刚经》之前周,广说行六波罗蜜,破四相,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重心偏向於破外境法执。若是修为不够,容易以为是「我」在那儿「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心」,所以需要在後周进一步破内境我执,达到「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之化境,方是真正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无著此说,骊龙探珠,尽得二周说之精华。在笈多三藏将其译出之後,中国佛教僧俗二界,虽有极少数人执持异见(如明如观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笔记》公然嘲笑前後二周,「不过换汤不换药」;明元贤之《金刚略疏》更是指责二周说,「今强於不异中求异,穿凿甚矣。」),极大多数人是接受并发展了无著之立论,其集大成者有二位,一是唐人吉藏,一是近人江味农。
吉藏之《金刚般若疏》,屡设问答,辩论二周,前後不下数十次。文繁无法全引,兹按其序,简说如下∶
(1)前说实智(实慧),後说方便智(善权)。
这是比照《大般若经》而言。既然《金刚经》是《大般若经》之一会,则其精神必定相通--
「问曰∶圣人制作,理致玄远,辞即巧妙,岂当一轴之经,遂有二周烦长?答曰∶虽曰两周,其旨各异,非烦长也。所以者何?类如大品两周,前周明於实慧,後周辨於善权。」
《大般若经》之「两番嘱累」,前说般若体,後说般若方便,为《大智度论》明确说出,自魏晋般若学兴,僧界学界,从无异议,故《金刚》之旨,亦复如此。
所谓「实智」、「实慧」、「般若体」,是从佛的境界说,怎样才算成佛;而「方便智」、「善权」、「般若方便」,则是从人的实践说,怎样才能成佛。实权相应,理行相契,方为完整。
(2)前为利根说,後为钝根说。
利根之人,悟性天成,故只须指明何为般若,即能一切皆了;钝根之人,若无具体指引,恐尚误入歧途,必须再设方便。故此利钝之说乃是实权之说的延伸。
「就此正说,开为二周,第一周为利根人,广说般若;第二周为中下根未悟,略说般若。作此开文,惊乎常听,今具引事义,证其起尽。
┅┅
问∶前说後说无异,云何前说为利根人,後说为钝根人耶?答∶大意乃同,其中转易形势,故钝根闻之,仍得了悟。如一种义,作此语说之不解,更作异门释之,则悟。犹如一米,作一种食,不能食,更作异食,则能食也。虽是近事,斯乃圣人制作之大体也。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力,为之立异字,即其证也。」
但吉藏的「米作异实」之喻,有点走样。严格而言,无论此食彼食,於米而言,都是方便--言下之意,利根一方便,钝根一方便,怪不得明人有「不过换汤不换药」之讥(如观引中峰明本之言)。
(3)前说尽(净)缘,後说尽观。
较前二说而言,此说直承无著之旨,不但於《金刚经》之微言大义,而且於佛法之宏旨,抉发无遗。後世持此说者,为数最多。
「今之两周,在义亦异,前周则净於缘,後周则尽於观。然要须缘净观尽,不缘不观,无所依止,方能悟於般若。故肇公云∶「法无有无之数,圣无有无之智。」法无有无之数,则无数於外。圣无有无之智,则无心於内。於外无数,於内无心,彼已寂灭,乃阶其妙。影公云∶「万化非无宗,宗之者无相,虚宗非无契,契之者无心。」故至人以无心之妙慧,契彼无相之虚宗,此则内外两冥,缘智俱寂。
┅┅
问∶何以得知前周尽缘,後周尽观耶?答∶经有明文,论有诚说。前经直云,虽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正叹菩萨依般若,作无所得发心,乃至无所得修行。而经意虽复缘观俱息,但文未正显灼破於观主,故钝根之徒,由言有於菩萨巧度众生,巧能修行。故後周经文,方息四心,无发心人,乃至修行者。然前周正劝生四心;後周明四心亦息,岂不然乎?论偈云∶於内心修行,存我为菩萨,此则障於心,违於不住道。以是义故,当知此文,正息观至尽於观主,文义炳然,无所疑也。此之二周,非止是一经之大意,乃是方等之旨归,至人环中之妙术也。」
吉藏具体落实了无著的论注,所谓「尽缘」,即是「生四心」--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一切外缘,悉皆是空。所谓「尽观」,则是「息四心」--连「无四相」之心也不起,「无发心人,乃至修行者」,内外尽空,无法无我,方是菩萨。短短四字,言简意赅,尽得佛法真谛,故吉藏大言炎炎∶「此之二周,非止是一经之大意,乃是方等之旨归,至人环中之妙术也。」
(4)前周成发心,後周泯发心。
这是把「尽缘、尽观」之说解释得更清楚些,「泯发心」者,无我是也。
「初章为二,前问次答。若约後会为论,则问意同前。昔来未依般若,不成发心修行,故今请问发心修行之义也。若约空观为论,则前问成发心修行,後问请佛泯发心,泯修行故也。
问∶前为成发心修行,後泯发心修行,将不相违耶?答∶终为成一意耳。由泯发心,乃成发心耳。若见有发心,不成发心耳。故前来成发心,即是泯发心,今泯发心,即是发心也。佛答中为二,初牒问明,发心即是缘尽义;从何以故实无发心者,明尽观也。」
(5)为前会众广说,为後会众略说。
「问∶二周说何异?答∶前广说,今略说;前为前会众说,後为後会众说。故大智论解无生品云∶问曰,前已说般若竟,今何得更说?答云,前为前来众说,後为後来众说也。如清凉池,前来者饮竟而去,後来者更饮也。」
不知为何,在前面数种解释之後,吉藏还要添上此说。佛祖於般若时开十六会说《大般若经》,其中第九会於给孤独园说《金刚经》,不知这儿吉藏所谓「前会」、「後会」究竟何指?
吉藏之後,匆匆千年,近人江味农,殚心竭虑,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重新论定二周说。与古人相比,江氏之特色,即在於富有新意,且清楚条理,有论有证。约而言之,江氏之二周说,为一总说,五分科∶
总说∶前说约境明无住,後说约心明无住。
「总之,全经之义,莫非阐发圆顿之无住。但前半多约境遣著。境者,一切相也。六尘、六根、六识,乃至空、有、双亦、双非,皆摄在内。故前半之义,可简言以括之曰∶一切皆非,於相不取。因不取,故皆非也。皆非而不取。则无明我见破,而观照般若之正智,焕然大明矣。後半则约心遣著。心者菩提心,三际心,有所发,有所得,一切分别执著等心,皆摄在内。故後半之义,可简言以括之曰∶一切皆是,於相不生。因不生,故皆是也。皆是而不生,则无明我见破净,而实相般若之理体,朗然全现矣。」
「故前半部总判曰∶约境明无住。至後半部所断,乃俱生细惑。故其总判曰∶约心明无住也。问∶此中已明离念,岂非已是约心明乎?答∶此有二义,前後不同。(一)此中虽已约心明,然尚属於诠理。(即谓尚属於开解。)入後乃是诠修。更於修中显义,以补此中所未及。此前後不同处也。(二)此中先离粗念,即起心分别之念。入後是离细念,即不待分别,与心俱生之念。此又前後不同处也。」
江居士之总括,有三处殊胜∶第一,他以「境」和「心」二个名相,很简明地概括了《金刚经》前後二周的重心差异,充实了无著的说法(无著说得实在太简单)。第二,他以「无住」二字概括《金刚经》之宗旨,以统领二周,以免读者只看差异,忘了其根本意趣是一致的。第三,如此总说,自然而合理地引出下面五个分科。
(1)前周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後周为已发大心修行者说。
「前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教以如何发心,如何度众,如何伏惑,如何断惑。後是为已发大心修行者说。盖发心而曰我能发、能度、能伏惑断惑。即此仍是分别,仍为著我,仍须遣除。後半专明此义。须知有所取著,便被其拘系,不得解脱。凡夫因有人我(即执色身为我)之执,故为生死所系,不得出离轮回。二乘因有法我(虽不执有色身,而执有五蕴法,仍是我见未忘,故名法我)之执,遂为涅盘所拘,以致沈空滞寂。菩萨大悲大智,不为一切拘系。故无 无碍,而得自在。此之谓不住道。所以少有执情,便应洗涤净尽,而一无所住也。」
此说即是前人所持「前为凡夫说,後为声闻菩萨说」之沿袭,前周破生死,後周破涅盘。对此,江氏在《金刚经》前後用语之不同中找到了证据,此乃是江氏之二周说的新意所在。
「後半部开章以来,但说发菩提,不说心字者,所以遣其执著此是菩提心之见也。苟执於法,便落我人四相,便非菩提心,故应遣也。至此则诸法空相矣。菩提心现前矣。故此处不曰发菩提,而曰发菩提心矣。应如是知见信解,不生法相云云,正所以显示发菩提心,必应如是。如是,乃为菩提心。即以结束前来遣荡不住发心之意。在令开如是知见,起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云尔。岂令不发菩提心哉。」
「前半部中,无论宝施、命施,概言福德,未言功德。而此则云前菩萨所得功德。前菩萨七宝布施,以功德称,必其已知离相修慧,非但知著相修福之人可比矣。因言功德,因称菩萨。」
这一见解,还有助於《金刚经》版本的校勘。一般坊间所见之《金刚经》流通本,校勘方面很少精到,如上述之「菩提」和「菩提心」,「福德」和「功德」,往往是不加区分的。
(2)前破粗执,後破细执。
粗细之分,乃明憨山之发明,其《金刚决疑》云∶
「〔解〕从此以下,徵破微细我法二执也。经初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者,以初发心菩萨,乃凡夫中大心众生始发度生之心,故种种著相,以依著自己五蕴色身修行。其所行布施,乃执著六尘粗物而求福果┅┅已前半卷皆此意也。其所破我依凡夫见起,即五蕴色相之我,其四相皆粗。今此经文以下乃是破已悟般若之菩萨,但能证之智未忘,以此执著为我,此是存我觉我之我,乃微细我法二执,四相皆细,故此经中标出一我字为首。但云我应灭度众生,更不言布施,是知功行已圆,唯有生佛之见未泯耳,故前粗後细。」【32】《金刚决疑》
憨山此说,颇有功於佛法,因为流行的对二周说的理解,人们往往会忽视前後二周的相通之处,简单地认定∶前周破法执,後同破我执--阅读《金刚经》,前周何尚不破我执?後周又何不破法执?所以正确的说法应是我法俱空,前後周的差别,在於「境」与「心」,凡夫与二乘,粗与细之分。江味农把这一点说得相当清楚∶
「当知我、法二执,皆有粗有细。粗者名曰分别我法二执,盖对境遇缘,因分别而起者也;细者名曰俱生我法二执,此则不待分别,起念即有,与念俱生者也。此经前半是遣粗执。如曰∶不应住六尘布施,不应住六尘生心,应无住心,应生无住心,应离一切相云云。皆是遣其於境缘上,生分别心,遂致住著之病。所谓我法二执之由分别而起者是也。故粗也。云何遣耶?离相是已。後半是遣细执,即是於起心动念时便不应住著。若存有所念,便是我执法执之情想未化。便为取相著境之病根。是为遣其我法二执之与心念同时俱生者。故细也。」
(3)前离相,後离念。
离相离念,应是传统成说,但江氏此处,又纠正了一个很容易产生的偏差--既然前为凡夫,後为二乘,则《金刚经》前浅後深。
不错,就修行而言,须得按步就班,由浅入深。
「此经前半部多言离相。相即是境,故总科标名曰约境明无住。後半部专明离念。(念,即见也。)念起於心,故总科标名曰约心明无住。此是本经前後浅深次第。今於前半将毕时,乘便点出见字。以显前後次第,紧相衔接。并以指示学人,修功当循序而进,由浅入深。此为世尊说著我见云云之深意,」
但若由此逆推,论为《金刚经》本身,也有前浅後深之差别,则是大谬也!
「前令离相,是遣其所执也;後令离念,是遣其能执也。前不云乎?所执之幻相,起於能执之妄见。故乍观之,本经义趣,前浅後深。然而不能如是局视者,因遣所执时,暗中亦已兼遣能执矣。何以故?若不离念,无从离相故。故前半虽未显言离念,实已点醒不少┅┅所以昔人有判後半是为钝根人说者,意在於此。谓利根人即无须乎重说。因世间利根人少,故不得不说後半部,令钝根者得以深入。此昔人之意也。不可因此言,误会为後浅於前。虽然,离念功夫,甚深甚细。若不层层剖入,不但一般人未易进步。即利根已知离念者,若不细细磋磨,功行何能彻底。如剥芭蕉然,非剥而又剥,岂能洞彻本空,归无所得乎?当知後半部自明五眼以後,愈说愈细。至於证分,正是令於一毫端上契入之最直捷了当功夫,所谓直指向上者。不明乎此,圆则圆矣,顿犹未也。若局谓後半专为钝根人说,於经旨亦未尽合也。此理不可不知。」
值得注意的是∶江氏在此批评了传统的利根钝根之说。笔者最初检索时,还惊诧江氏何以漏了吉藏列於篇首之利根钝根说?再仔细是考量,在立论上,利钝之说直接与凡夫二乘说冲突,所以江氏的二周说中没有采纳,有其充分理由。
(4)前说「二边不著」,後说不著「二边不著」。
「前半说,离一切相,方为发菩提心;方为利益一切众生之菩萨。是空其住著我法之病。後则云∶无有法发菩提,无有法名菩萨,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语。是空其住著我法二空之病也。故前是二边不著;後是二边不著亦不著┅┅遣之又遣,至於能所皆离,并离亦离,方证本来。」
此一说在用词和思维方法上,颇受禅宗影响。就立论而言,「二边不著」乃是中国佛学自三论宗以来的传统,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是也。至「教外别传」的禅宗兴起,方连「二边不著」也要破著。江味农居然在《金刚经》中找到了依据。
(5)前一切皆非,後一切皆是。
此说为江氏之发明,前人从无此说。
「前半部是明一切皆非,(如曰∶非法非非法,有住则为非住。)以显般若正智之独真。盖此智本一尘不染,而一切相莫非虚幻。故应一切不住,而後正智圆彰也。後半部是明一切皆是,(如曰诸法如义,一切法皆是佛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明般若理体之一如。盖此体为万法之宗,故一切法莫非实相,故应菩提亦不住,而後理体圆融也。」
对此立论,他也从《金刚经》本文的用词中找到证据∶
「前半部中,长老答辞,多言不也。即不答不也,亦从无答如是者。後半部惟开佛知见中,答如是最多。(此外只有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一处,言如是。)此经字字皆含深义。可知凡答如是,决非泛言。实承前已说者,表示诸法一如,一切皆是之义耳。」
乍一看,江氏此说,颇为突兀,令人有「过尤不及」的担心--佛法圆通,何能将一经截然分开,说一半「一切皆非」,一半「一切皆是」?但就《般若》经义而意,江氏此说似乎有理,近人汤用彤教授曾有一段极精彩的议论∶
「《般若》《涅盘》,经虽非一,理无二致。(《涅盘》北本卷八,卷十四,均明言《涅盘》源出《般若》。)《般若》破斥执相,《涅盘》扫除八倒。《般若》之遮诠,即所以表《涅盘》之真际。明乎《般若》实相义者,始可与言《涅盘》佛性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51页)
若在遮诠的立场上理解「一切皆非」,在佛性的立场上理解「一切皆是」,江居士之说,大有深意焉!
关於《金刚经》二周说,吉藏和江味农,足以涵盖古今,凡有所说,皆逃不出二家已述。但有一特例,则非提一下不可,那就是沈家桢博士的<「云何应住」和「应云何住」>一文。
返
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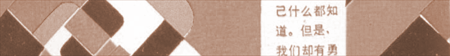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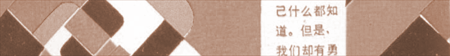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2896
010-62912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