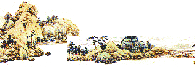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张光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大山和小山多次劝他住医院他都摇头拒绝。那日,小山回家看望他,张光源坐在院子里的木椅上,披着棉衣,头低垂着,象勾头菜一样抬不起来。听见有人进大门,他头一歪,脸朝大门的方向一看,见是小山,喘着粗气,吃力地说:“小山,你回来了。”小山听见爹问,心里惊喜,爹虽病重,声音还是先前那么大,那么宏亮。小山走到张光源跟前,亲切地叫了声“爹”。 张光源慢慢地抬起沉重的头,但脖子依然没有伸直,好象是头太重而脖子太软。由于张光源的头没有完全抬起,他眼珠上翻,极力想看清楚小山的脸。这时小山看清了爹的脸,眼皮浮肿,眼珠布满了血丝,道道血丝就象地球仪上的国界和公路线,纵横交错,蛛网一般。目光是呆滞的。脸色黝黑,嘴皮乌紫,不停地喘着粗气,那样子看上去十分难受。小山的心里一阵痉挛,眼泪从心底涌出,顺着眼角直流。 “小山,你、你回来了。”张光源重复着刚才说过的那句话,由于气喘说得不是那么连惯。 小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流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哭啥?你回来了,咱爷们见见面,摆摆话,就好。”张光源的头又低下了。 “小山。”惠贤回来了,胳膊上挎着一大篓子麦秸。她又黑又瘦,身子微微向左倾斜,她是使尽了全身力气才挎起那一大篓子麦秸的。 小山答应了一声,急忙上前接过娘胳膊上的草篓子。 “快,喂吧,牛都饿了。”张光源催促着,他的声音里带着抱怨。 “我去喂。”小山走进了牛屋。 “还得铡。”张光源说:“你不会喂。叫你娘喂。” 惠贤支起了铡刀,蹲在地上,大把大把地整理着麦秸,那些零乱的光滑似冰的麦秸到了她的手上都变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整整齐齐的了。自从张光源生病后,惠贤承担了沉重的农活和全部的家务,连铡草这种男人们干的事儿她也掌握得如此熟练。嚓--嚓--嚓--铡刀发出缓慢而有节奏的响声。 “娘,平时谁来跟你铡草?” “还会有谁?”娘停顿了一下说:“丙进(老闷)。全靠那娃子。” “你咋不叫嫂子来喂?” “靠得住啥,还不如外人。”娘的声音冰冷,没有丝毫感情。“一个也靠不住。” 大山大学毕业分在城关中学教书,他的媳妇跟爹娘分灶吃饭,算是两家人。张光源喂这头牛是两家共用,因此小山认为他嫂子该来喂牛。小山没想到娘会说出“一个也靠不住”的话,这句冷漠的话语意味深长。小山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在发烧。不是吗?他平时月儿四十才回来一回,而且象住旅馆一样住上一夜就匆匆地走了,爹娘需要他时他又在哪里呢? “娘,咱家不会不喂牛?”小山转换了话题。 “不喂?你爹会愿意?这牛比他的命还金贵。” 麦秸铡完了,惠贤给牛拌饲料。小山坐到了张光源的身边。 “爹,明儿我送你到医院去。” “去那儿弄啥,我知道我不中了,咱不去白花那钱。” “爹,钱你甭操心,我有。” “不憨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可不能乱花。我心里清楚,我过不去这一关,早晚也得走这条路。你们给我做的木头(棺材),我躺在里头试了试,大小长短都合适。这次你回来,寻个人把档头上刻个‘福’字,用油漆油一下。”张光源一直没抬头,连眼也没睁,断断续续地跟小山说着,累了,他就停一会儿,有力气了又自言自语地说几句。“我死了,装在木头里,钉盖时一定记住把蒙在脸上的手巾揭下来,不然下辈子就要变成憨子。你可要记住。埋时,简单点,随便埋了就中了,不要叫响器(乐队),不要乱花钱,挣个钱不容易。”张光源说这些话时很冷静,没有一点儿悲伤,好象他在世上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没有啥可惦记,也没有啥值得留恋。无牵无挂,没有遗憾,没有惧怕,面对死神,他是那么勇敢,那么坦然。在跨过人生最后一道门槛时,心情如此之平静。张光源的语气越平静,小山的心里越难受,忍不住泪如雨下。张光源听见了小山的抽泣声,微微地睁开眼睛,慈祥地望着小山。“哭啥?死,谁都躲不过。从百姓到皇帝,没有长生不老的。都得死。去吧,你走了这么远的路,该去歇歇了。”张光源又闭上了眼睛。 正午,阳光直射到院里,小山浑身发热,但张光源还穿着厚厚的棉衣,好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季节里。张光源没有穿袜子,腿和脚都是肿的,小腿透亮,脚面肿得象螃蟹。脚肿得太大,无法穿鞋,光着脚踩在一双旧布鞋上。两只粗糙的大手搭在膝盖上,手指甲很长,脚趾甲也很长,象海滩上暴晒已久的贝壳,干燥而发白,没有丝毫的光泽。张光源的胡子也很长时间没有刮过了,一根根支叉着,足足有二指长。小山端来了一盆水,给张光源洗了脸,洗了手,然后轻轻地把张光源的脚放在盆子里。小山用刮胡刀小心翼翼地给张光源刮了胡子,接着又给张光源剪了指甲。张光源摸着下巴,脸上浮出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胡子刮了,摸着透美。”张光源说。 张光源是很爱整洁的人,不管衣裳好赖,那怕是补钉摞补钉,只要出大门,他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夏天再热,张光源从不打光膀子。三伏天,不管是干活还是歇凉,村里的男人都是穿着裤衩,光着脊梁,张光源从不这样。为这,惠贤还跟张光源争吵过,说张光源是假斯文,怕衣裳穿不烂给旁人撇下。张光源大发雷霆,把惠贤臭日噘了一顿。这件事,小山记得清清楚楚。小山受了张光源的影响,这方面的习惯与张光源一模一样。 日头快落山了,院子里没有了阳光,风起了,吹得桐树叶沙沙发响。 “咱进屋吧。”张光源说。 小山把爹扶进屋,张光源慢慢躺在床上,刚躺下,出气就有些不对了,喉咙里就象拉风箱,脸憋得乌青乌青。张光源无法仰卧,在小山的帮助下翻过身趴在床上,两只胳膊支在胸前,头向下勾着,双膝跪在床上支撑着身躯,脊梁拱得高高的,整个身子就象一座拱桥。样子十分难受。张光源不时发出粗声的气喘和哎呀哎呀的呻吟,大约持续了一袋烟工夫,张光源支持不住了,又从床上下来坐在椅子上。 屋里点燃了煤油灯,灯火如豆,昏黄暗淡。 惠贤端了一碗面叶汤进来,她用筷子挑起一块面叶呼呼地吹了两下,喂进张光源的嘴里,张光源嚼得很慢,象在品味着什么,然后脖子一伸咽了下去。一块面叶下肚,突然又气紧起来,呼吸困难,张光源用手推了一下碗,显得很烦躁。 小山说:“爹,再喝两口。” 张光源摆摆手,没有说话。 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大山回来了。他进屋看过爹,然后走出门向小山摆摆手。小山会意,立即也走了出去。 大山说:“你看咱爹的病咋弄?” 小山说:“我看干脆把咱爹送到平川市医院。” 大山说:“恐怕不中,咱爹老犟。我跟他说了几回,他都不听,他就信火燕的。” 小山问:“火燕跟咱爹说啥了?” 大山说:“那天你不在家,火燕来了,给咱爹摸了摸脉,看了看舌头,翻了翻眼皮,然后说,‘老哥,咱兄弟们谁也不倒谁,实话跟你说,我看你是不中了。啥也甭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甭心疼那钱。好赖两个侄儿在外面工作,挣得来。’从那天以后,咱爹那里也不去,在家里等着……” 小山说:“火燕知道球,他就会给人扎扎针,治个腰酸背痛,咱爹这病他懂?” 大山说:“可咱爹老信他。那几年咱爹跑南山做生意,火燕也跟咱爹到南山采草药,有一回火燕掉到山底下,咱爹救了他,他跟咱爹交情很深,咱爹病后,火燕三五天总要来看一回,咱爹想着不管咋说火燕不会倒他。” 小山说:“再跟咱爹说说试试。” 大山说:“那中嘛。” 兄弟俩先后进屋,站在张光源跟前。 小山说:“爹,我跟哥商量了,明儿送你到平川市医院,寻个好医生看看。” “看啥咧,有啥看头。火燕都说了,是老了,不中了,叫甭白花那钱。”张光源断断续续地说。 “你听他弄啥?他光会扎针,你这病他不懂,要是早点到大医院看,说不定早好了。”小山说。 “你说得轻巧,我不去。生了病要都能治好,那不憋破世界?”张光源看了一眼小山,接着说:“再说,我要是到了大医院去看,叫火燕的脸往哪儿搁?连我都不信他,谁还信他?” 无论大山小山咋说,张光源就是不听,两人无奈,只有叹气。 其实,大山和小山并没有完全弄清张光源的心思,张光源之所以不到医院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怕死在外面。死在外面,就成了孤魂野鬼,即如是尸体拉回来埋在自家坟地,但魂是无法随之归来的。更何况城里人兴火葬,人死了往火炉子里一扔,呼呼一阵大火,高烟筒里冒出一股白烟,就剩下一把白瓷拉拉的骨渣子。张光源怕魂丢在外面,也怕火烧,但他不怕死。用他的话说,人老了就该死,生老病死,就跟天黑天明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老了要是都不死,这个世界也就盛不下了,迟早都要被憋破。不光张光源是这样想的,山里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山里人老了,生病了,很少有人去医院求医,就躺在床上,哼哼嗨嗨等着见阎王。老年人都是这样死的,自然张光源也不会破这个例。 夜深了,张光源睡了。大山走了。劳累了一天的惠贤闭着眼睛歪在了床边。小山毫无睡意,坐在他爹坐的椅子上,看着自己的爹和娘。唉,人老了竟是这样……小山的心里酸酸的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大山,大山。”张光源突然大声喊叫。 “爹,爹,你叫啥?”小山知道爹不是在叫哥哥而是在叫娘。 张光源睁开眼睛看了看,啥也没说,又闭上了眼。 “大山,啥事?”惠贤被叫醒了,睁开了疲倦的眼睛。 张光源闭着眼吭吭吃吃地说了一长串,小山什么也没听清,只听到了一个“牛”字。 “饮了。你睡吧。”惠贤说。 张光源呼呼地睡了。 “娘,爹问的啥?” “问牛饮了没有。” “爹也是,都病成这样了,还应记那牛。” “你爹就这样,除了牛,他心里啥也没有。” “我爹太犟了。” “他一辈子就那脾气,不管啥事儿,他爱认死理儿,他认准了,用骡子用马也拉不回来。” “我爹也太信火燕了。” “他信火燕,也信命。前年,瞎子李先生给你爹算了一卦,说他过不去今年这个关口。” “瞎子是胡诌,算得准啥?” “可你爹老信。” “我爹救了他(李先生)的命,他现在又来害我爹。” “他害你爹弄啥?他跟你爹又没仇。再说,命这东西又不能不信。那年李先生给老闷算了一卦,说老闷八字里有灾星,是牢狱之灾,这不,老闷坐监,不就应了。” “小山,小山。”这次张光源是在叫小山。 “爹,啥事儿?”小山走到床前。 “你去找李先生再给我算一卦,看还能活多少日子。哎呀……” “爹,你信那弄啥?别说李先生,谁也算不准。” 张光源本来没睁眼,听小山这一说,立时瞪起了眼睛。小山见状,赶紧改口:“爹,天明我就去。” 小山本不想去找李先生,但他又怕爹生气。爹已经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临终前向他提出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当儿子的能拒绝吗?小山想在哪里躲一天,给爹编一套瞎话,瞒过去,但他又不忍心欺骗一辈子善良从不说瞎话而又最恨说瞎话的人的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