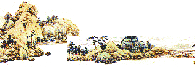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王彩珠的改嫁,在槐树沟掀起了轩然大波。新社会,寡妇改嫁本属常事,但象王彩珠这样儿大女成人又是这么大年龄的老太婆改嫁在槐树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于是,村里的人议论纷纷,把王彩珠改嫁的责任全推在范娃身上。 “范娃啊,不算人,把他娘都逼嫁了。” “听说他娘不愿意嫁,哭了一夜,都给范娃跪下了,范娃的心软都没软一下。” “你没看见,他娘走时还在他爹的坟上哭了半天。” 村里的人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范娃大逆不道,说了范娃一百个不是。说得最凶的还是何姓人家。何五爷已经八十多岁了,身子还算硬朗,他没有过世,也没有让位,还继续担任着何家的族长。这些年,何家老是出事儿,先是何金柱吃石头面坠断了肠子,接着是茶花被糟蹋何大流坐监,再后来是何大流的腿被打断房子被大水冲垮,现在又冒出范娃他娘改嫁,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何五爷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通这个理儿,是他这个族长没有当好,还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的族长没当好。要是从何大流偷那半个铁锅他就硬起来,用一次家法,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退一步说,何大流偷铁锅他忍让了,何大流砍祖先栽的大槐树,砍坟上的古柏说啥他也不该再让,就这样三让两让,让出了一串串祸事。范娃把他娘逼嫁了,这回说啥也不能再让了,何家的人要象家人,就得从这件事儿开始,重新整治。何五爷下了决心,要治一治范娃了。不然不知后面还要发生些啥子事情。何五爷叫孙女燕子去把范娃的大伯、何大流、二喜叫到他家里,说:“你们都听说了吧?范娃他娘昨天背着包袱走了。” 三个人都说听说了。 何五爷说:“这下好啦,咱何家又出了一个大‘孝子’。” 何五爷的脸色非常难看,没有一丝儿红色,苍白得象死鸡的脸。 “你们说这事儿咋办?”何五爷死鱼般的眼睛看着象哑巴似的三个人。 “五叔说咋办就咋办。”三个人象商量了一样回答。 何五爷山羊胡子一撅,拐棍在地上一剁,嘴唇颤抖着说:“我说咋办就咋办,叫你们来弄啥咧?!” “那就按家法。”范娃他大伯说。 “按家法。”何大流说。 “按家法。”二喜说。 晚上,没有星也无月,漆黑一片。何五爷的大院里的弯弯枣树上挂着一盏鬼火似的马灯。马灯下,一把古老的油漆剥落的箩圈椅上坐着一个瘦筋筋的象烧火棍一样的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手里捏着一根雁脖子拐棍,神情严肃地等待着何姓子孙向他朝拜。这是何姓的家族大会,每年七月十五祭祖时召开一次。今天是特别会议,人也到得特别齐。坐在何五爷的院里,黑压压一片,寂静无声,连出大气的也没有。 当当!何五爷把拐棍在地上使劲敲了两下,抬起拐棍往人群里一指,厉声吼道:“范娃,你出来!”何五爷沙哑的声音象纯刀子似的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在院子的上空鬼嚎般地飘荡。 范娃毕竟当过村干部,经见过大场面,何五爷的吼声没有吓着他,他从容地从人群中走出,面向大家站着。由于灯光暗淡,人们也看不清他的脸色。 人群一片寂静。 当当!何五爷的拐棍又在地上敲了两下。“你说!为啥要把你娘逼走?” “俺没逼她,是俺娘想走。俺也觉着俺娘该走。”范娃不慌不忙地说,声音不大但在坐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放屁!”当当!何五爷的拐棍在地上敲击着,声音比刚才还响。在弯弯枣树上夜宿的两只小鸟被惊吓得扑楞着翅膀飞走了。“你这个逆种,不说清楚,小心你的皮!” “五爷,你先甭噘……” “甭噘?那你就说。为啥逼走你娘?” “我说了,我没逼她。” 范娃说的是实话,他娘的改嫁纯属自愿。但也与范娃不无关系。王彩珠守寡十多年,早年与儿女在一起,日子虽贫,但也热闹。生活虽苦,但也不无情趣。后来茶花跟着康光辰走了,范娃又与她分了灶,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天天烧烧燎燎,这种日子就象井吧凉水没有味道。想说个话,身边没有人,就靠喂那一群鸡给她的生活增添一点生气。那天,不知范娃发的那门子邪火把她的大公鸡杀了,为这事她呕了几天气。后来她听说范娃把断了腿的无头公鸡甩在了何大流的窑洞外,她才知道范娃为啥要杀那只大公鸡。从那以后,她害怕见儿子,每天儿子下地了,她才开门,儿子要收工了,她就关上门。从不与儿子照面。但她与儿子住在一个院里,躲躲藏藏总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她选择了改嫁这条路。 “没逼她?没逼她她会走?你爹死了这么多年她咋没走?偏偏跟你吵了架就走啦?这不是你逼的又是啥?” “五爷,这事儿不好说,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没逼她。” “我看不用家法你是不会说实话!” 所谓的家法,也很简单,不知是哪一代哪个祖宗制定的--打嘴巴。这种家法的目的不是叫受惩罚的人受多大的罪,而是叫受惩罚的人在众人面前丢丢脸。这种家法一直沿用至今,后代人无所创造,无所发明,也无所前进。 何五爷宣布后,范娃的大伯从人群中走出来,啪啪!给范娃了两个嘴巴。他是范娃他爹那一辈的,又是老大,今后要是何五爷一命归西就该他管这个家了,所以,他不得不先站出来起一下示范作用,也借机显示一下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使这些人以后不至于小看他。范娃的嘴角流血了。耳朵唧唧直叫,眼里冒着金花。范娃打了个趔趄。他万万没想到他大伯会出手这么重,大概是因为自己过去得罪了他。范娃的大伯打过范娃后,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了。何五爷见状,气得从箩圈椅里站了起来,瘦削的身子不住地颤抖,连手上的拐棍都在左右摇晃。 “死啦?你们都死啦!”何五爷大发雷霆。“何大流,你还坐着弄啥?” 何大流不想打范娃,这个隐情只有他知道,范娃是他的儿子。何大流又想打范娃,倒不是因为范娃打断了他的腿,而是范娃逼走了他的娘。王彩珠走前,悄悄地跟他说了,鼻一把泪一把的惨相何大流终生也无法忘记。王彩珠说,大流,范娃啥事儿都知道了,我无法再面对他。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现在我最放心不是的就是你……何大流拉着王彩珠形同枯槁的手泪 流满面 。何大流正在回想着王彩珠临别时撕心裂肝的一席话,何五爷也就是他的五叔点了他的名字。范娃听见何五爷喊何大流,心里早有准备, 两腿一叉,立稳桩子,做好了挨打的架势。使范娃没想到的是,何大流的手象拍苍蝇一样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一点疼的感觉也没有。何大流打了范娃,象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心里顿感轻松,一瘸一拐地走向原来坐的地方。范娃疑惑不解地看着何大流左右摇晃的身子。 二喜怕何五爷点他的名,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间,吓得连咳嗽一声也不敢。 何大流打了范娃之后,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了。何五爷气坏了,他这个族长的话没人听了,于是骂了一句,但谁也没听清楚他究竟是骂范娃还是骂不打范娃的那些人。何五爷亲自动手了,他抡起了手里的拐棍照着范娃劈头盖脑地就打。范娃伸手挡住了何五爷从空中劈下来的拐棍。 “五爷,你知不知道打人犯法?” “屁!我倒要看看犯啥法?”何五爷说着又抡起了拐棍。 当当!拐棍敲击着地面。何五爷气急败坏地吼道:“听着,明儿清早,都到坟上!” 二喜知道何五爷下狠心要整治范娃了,散会后他连家也没回,悄悄地去找张光源,叫他想办法阻止何五爷,使范娃免遭不幸。张光源想了想,十分为难地说,这是你们何家的家事,外人没法插手。二喜很失望地走了。那夜,张光源也没睡好,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范娃惨遭不幸,于是天刚亮他背了个箩筐装着下地割草而跑到了公社。 坟上,何家老少百多口人,站在那里黑压压一片。他们象吊丧一样一个个低着头。 何五爷命范娃跪下,范娃死活不跪。 “捆起来,不信治不了他!”何五爷发话。 范娃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了。在何五爷的亲自指挥下,范娃被捺在他爹的坟头前跪着。何五爷叫范娃向他爹认罪,范娃脖子硬着不住地摇晃着肩膀弹腾着双腿一个字儿也不说。 “用石板把他的腿压上!”何五爷的拐棍指着一块供桌(祭祖时用的青石板)。 范娃的小腿被一块石板压上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头上的汗珠黄豆那么大一颗颗往外冒。当他被松了绑之后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公社的干部来了,但为时已晚,何家的坟上已无一个人影。公社来的干部问明了情况,把何五爷带走了,既未戴手铐也未捆绳子。 范娃成了拐子。从此,村里的人都叫他小拐子,称何大流为老拐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