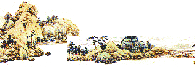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这几天,张光源的脸上有了笑容。大山的媳妇娶过来了,尽管他弄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他心里还是高兴的。娶了儿媳妇他就该当爷爷了,想着要当爷爷,心里透美。山里人有球啥,吃好吃赖只要肚子不饥,穿好穿赖只要身子不冷,图的是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他当了爷爷也就儿孙满堂了,他心里咋会不美?你看那何大流,一辈子偷鸡摸狗不干好事儿,落了个啥?媳妇跑了,腿也瘸了,生了个娃子还没养活,绝户了。绝户头多难听!断了祖上的香火。他张光源虽然身上有点饥荒,那也是为子孙打下的,该。范娃也娶了媳妇,但他的心情却大不相同。娶媳妇他姐夫给帮补了些钱,可还是塌了一屁股饥荒。黑了他搂着媳妇睡着怪美,白日他想着饥荒怪愁。这几天不断有债主上门要账,范娃的脸总象蛋皮(阴囊)一样枯抽着,心里焦得慌。二喜活得还算滋润,他的娃子小还不该说媳妇,没啥愁的。媳妇赵大脚扇扇火火,家里地里来回窜腾,二喜倒真的没啥心可操。喝了汤,碗一放,掂着烟袋串门去了。二喜的屁股沉,到哪家都是一喷大黄昏。这不,天还没全黑,他就捏着旱烟袋背着双手,烟布袋在屁股后头滴溜着象个牛蛋一样一摇一甩进了张光源的家。 “三哥,”按张家的辈份排,在“光”字这一辈人中张光源排行老三。二喜前脚进门后脚还在大门外就大喊了一声。 “哎。”张光源在屋里答应,“二喜,来,我正想找你呢。” “有啥事儿?”二喜进屋坐下。 “这两天秋要收完了,杀苇子还得十天半月,我琢磨着抽空咱开个会,商量商量今年这苇子咋弄。”年初队干部改选,张光源又当上了生产队长,二喜变成了副队长,范娃还是政治队长。张光源死活不干,公社书记曾跃旗还专门跟他谈了话,说不能辜负社员们的心愿。张光源说一家人不能两个当干部,他当队长,小山就不能当会计,小山当会计,他就不能接这个队长。为这事儿又开了一次社员大会,社员们认为张光源说得有理,就叫范娃兼生产队会计。张光源接任队长后除了一门心思抓生产,还动起了搞副业的脑筋。现在不准做生意,做生意就是偷鸡倒把,他不敢做,也不敢叫社员们去做,他怕犯政治错误。生意不准做,但社员自己家里养的鸡和鸡下的蛋政府又准拿去卖,这不犯法,因为是自己养的。由此张光源想到了编席。苇子是自己生产队的地里长的,自然可以编成席拿去卖,就象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是一个道理。张光源反复想过之后,决定今年的苇子不分给社员,全部编成席,然后把席分给社员,愿用愿卖由自己。所以,张光源想跟二喜和范娃商量商量。 “咋弄?还不是照老规矩,按人头分。”二喜不加思索地说。 “分,简单。可一分下去,都扛到集上稀粑烂贱卖了,划不着。” “那咋弄?” “依我看,编成席。” “编席?恁些苇子,哪来恁些匠人?” “要商量的也就是这事儿。”张光源用手裹了一根纸烟递给二喜说:“看能不能把范娃他姐夫请回来。” 二喜点燃喇叭筒似的烟卷,滋溜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哎呀,你这烟还怪恶咧。是不是你栽的兰花叶(一种烟草名)?” “是。好不好吸?” “好吸,把烟种籽给我留点。”二喜又吸了一口细细地品味着。“范娃他姐夫,靠他一个人中球!” “靠他一个人是不中,那咱不会把他当成烟种籽。” “哦,你是说叫他当师傅?”二喜明白了张光源的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你去把范娃叫来,咱再商量商量。” 自从二喜的政治队长被刘左左撤了后,二喜还真的松了一口气。政治队长,官不大,还真不好当。光是叫他站在红宝书台前念一条最高指示就够他喝一壶的了。二喜没当政治队长,生产队长照干,所以,他根本不恨刘左左。后来他又被选成副队长,他也没有怨气,他佩服张光源,张光源敢说敢干有骨气。现在他跟张光源和范娃搁伙计,张光源是主心骨。 范娃跟在二喜的屁股后头进来了,喊了一声“三叔。” 张光源说:“坐吧,范娃。咱商量个事儿,刚才我跟你二喜叔说了,今年咱队里的苇子不分也不卖,咱成立个副业组,编席。我算了一下,卖席比卖苇子要多卖四五倍的钱,大家的收入都要增加。就这事儿,你俩看中不中?” 范娃说:“我看老中。可就怕上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范娃是政治队长,他想到的是政治。 二喜说:“咱不说,上头知道个球。咱把‘尾巴’藏起来,看他割球啥?” 范娃说:“咱村的人老球样,爱往上头拱。要有人往上头一拱,恐怕纸包不住火。” 张光源说:“范娃说这也是实话。咱村人穷,吃亏也就在这上头。那一年,我当队长,一人多分了五厘自留地,不知道谁去上头拱了,我的队长被撤了,大家的地也退了,谁也没得到好处。越拱越穷,越穷越拱。有一句话叫槽里无食猪拱猪,拱来拱去还是拱的自己。你们看央桥,地不比咱村多,也不比咱村好,可人家那日子比咱村的人过得滋润。为啥,人家村的人能,不拱。开点小片荒,做点小生意,木匠,铁匠,泥水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干各的,谁也不攀扯谁,谁也不拱谁。上头派人去查‘五匠’,割‘尾巴’,人家不但不拱,还互相包着,说‘尾巴’早就连根挖了,现在长不出来了。结果得到好处的还是大家。人家能就能在这上头。咱再看看人家那村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打光棍的。再看看咱村,从南到北扳着指头数数,说不下媳妇的也不止十个八个,这又是为啥?不是咱村的娃子丑,也不是咱村的娃子憨,是老穷。谁家的闺女愿来过穷日子?越穷,说媳妇越得花钱,不花钱怕人家不跟你。日子越好过,人家的闺女还偏偏不要钱,怕要钱你不要她。说穿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我琢磨了多日子,今年咱村的苇子不能分,编席。咱开个会,跟大家说清楚,谁要去拱就叫他去拱,我这队长再叫他撤一回。” “三叔说得在理,就照三叔说的干。”范娃说:“要撤连我这政治队长一齐撤。” 张光源说:“那这事儿就这样定了。光有砖瓦没有匠人,这房子还是盖不起来。范娃,你去把你姐夫接回来,咱这副业组还得靠他领。” 范娃说:“中。” 槐树沟的副业组成立了,范娃当组长,小山当副组长,康光辰当师傅。年轻人听说学编席,挤破脑袋往副业组里钻。以前他们想学,康光辰就是不教,全村只教了一个小山。副业组报名的人太多了,范娃拿着不好办,跟张光源说:“三叔,我看干脆一家来一个。” 张光源说:“一家来一个还是有矛盾,有的家人多,有的家人少。我看这样,愿意来学的都叫他们来。” 张光源这样一说,不光小伙子们来了,一些年轻妇女也来了,闺女中带头报名的是何燕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