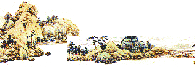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上头出坏人了。县长是历史反革命。县长的上头有坏人,县长的下头也有坏人。大山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从县城带到了公社,带到了槐树沟,平静的山村也就不那么平静了。县长叫张常理,槐树沟的人大多都认识他。大亚在成立人民公社以前是区政府,那时张常理是区长,张区长很和蔼,样子象个庄稼人,经常到这个村看看,到那个村转转,吃饭也在老百姓家里,有啥吃啥,不挑不捡。槐树沟的人对张区长印象很好,咋着当了县长还会成反革命,成了坏人,槐树沟的人弄不懂。但消息是大山从县上带回来的,大山不会说瞎话,县长那么大一个官,大山也不敢乱说。 大山是神佑县造反司令部的宣传部长。他还是个中学生,咋着就当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的官有多大,槐树沟的人是不知道的,但槐树沟的人知道宣传部长是个官。还在读书的学生就当了官,这究竟是咋回事,槐树沟的人更弄不懂。那天公社召开贫雇农代表大会,二喜去了,他是槐树沟的贫雇农代表。二喜看到大山戴了个红袖套,站在台子上跟贫雇农代表讲话,他好象长高了些,嘴也很会说。大山说,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以实际行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务之急是在机关在工厂在学校在农村建立无产阶级造反派组织,破“四旧”立“四新”,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大山说,县上的运动已经搞起来了。我们的司令部已经揪出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大坏蛋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常理。在破“四旧”中,我们首先改了县名,神佑神佑神仙保佑,这县名多么封建!我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司令部的决定,从现在起,神佑县正式改名为红卫县!请大家记住并广为宣传。“红卫”就是红卫兵的“红卫。”也就是这个县要成为红色的县,成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县,成为造反的县,成为我们红卫兵的县!大山讲得慷慨激昂,最后他宣布大亚公杜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接着宣读了红卫县造反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衡来山为大亚公社红卫兵总部司令。他还要求各大队要尽快建立红卫兵战斗队,由贫雇农代表担任战斗队队长,发展战斗队队员,拆庙砸神,批斗坏人。这是大山第一次回公社宣传造反的道理,播撒革命的火种。 会开完了。二喜在公社饱餐了一顿,心里挺高兴。回家的路上,他想得很多。张光春倒了,槐树沟又出了一个比张光春还大的官。连他这个几十年连衣裳都没穿伸展的人也要当什么红卫兵战斗队队长。他可是从来都没当过官,如今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了,没想到从天上落下一顶官帽来,二喜有点大器晚成的感觉。更使他高兴的是,大山在会上发给他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红红的,亮亮的,周围还放射着万道金光。他如怀至宝,别在胸前,走起路来胸脯挺着,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由于他高兴,边走边哼着小曲儿,喉咙里不时冒出一个臭饱嗝,打断他喉咙里哼出的小曲儿。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也没有这么可心过。旧社会先死了爹后死了娘,倾家荡产予以安葬,使他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的家变得更穷了,变得家徒四壁,响也响不起来了,就是在屋里打个屁也无遮无拦。媳妇也说不下,打了多年光棍。后来遇到了嫁不出去的赵大脚,好赖娶过来成了一个家。有了媳妇,二喜那种当光棍时养成的浪荡习性一点没改,象没有长大的娃娃,喜爱热闹。哪儿热闹他就往哪儿去,哪儿人多他就往哪儿钻,哪儿有戏他就往哪儿跑,哪儿有说书的他就往哪儿窜……他说得上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物。村里的小娃子们都喜欢他。那些小娃子们想去看戏,看电影,天黑,怕走夜路,都会去叫他,说,二喜叔,咱去看电影,二喜总是那句话,中。说罢,不管肚里吃饱没吃饱,碗筷一丢,说,走。那些小娃子们就一串串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象战争年代的儿童团。范娃和小山都是他屁股后头的常客,他俩也亲切地叫他二喜叔。自从二喜当了贫雇农代表,吃救济粮,发救济款,上头从来没少过他,他也落得喜欢。他觉得穷有穷的好处,富有富的坏处。穷户人家不怕贼,他出门从来就不锁门。富户人家就不一样了,得时时操心,时时防贼。遇到运动了,更是提心吊胆。他穷惯了,也尝到了穷的好处。过年了,没得吃,政府还记挂着他,给他救济粮,给他救济钱。这不,这阵儿又给他救济了一个官儿,给他个战斗队队长当当。要不是穷,他能当到贫雇农代表?要不是贫雇农代表,他能当到战斗队队长?要不是战斗队队长,他能吃到这顿喷香的肉?他能得到毛主席像章?他为穷而高兴,为穷而自豪。他用手摸了摸别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又打了一个饱嗝,一根粉条象虫一样从喉咙里钻出,他嚼了一下,还蛮香。中午,衡来山衡司令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粉条熬肉,他多吃了一个份,是大山给的,吃完了,他觉着肚子有点撑,但他心里高兴,他觉得大山看得起他。大山这娃不赖,在造反派里当了那么大个部长,还没忘记他这个老叔,这娃子一定会有出息。二喜边走边想,值,值。当贫雇农代表还真不赖。但他又有些发愁。战斗队队长还有恁些事,发展队员,拆庙砸神,批斗坏人……他没念过书,他不知道这些事该咋干。想到拆庙砸神他的心里就咚咚直跳。北沟响潭上边的龙王庙,百里之内的老百姓都来这里烧香跪拜求雨求药,他要去砸,那些烧香的人会饶他?万一那些人脑了把他打一顿他不是白挨。还有斗坏人,谁是坏人?咋斗?都是挨邻侧近,几十年的老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斗了人家,还咋有脸见面?二喜越想越觉着这些事儿难办,他不想当这个战斗队队长,得把这个官儿让给谁。但贫雇农代表不能让,再说扳着指头数数,全大队还没有哪个有他穷,当贫雇农代表都还不够资格。至于把战斗队队长让给谁,二喜确实动了一番脑筋。让给范娃,他可以跟范娃他娘唠嗑两句,让给小山,他可以靠上大山这根杆儿。二喜权衡着,掂量着,最终还是决定让给范娃。让给范娃,实在些。他找范娃商量事情,还可以跟王彩珠说说话,跟女人说说话,心里美,并不一定非要有那种事儿。二喜在心里拨弄着小算盘,美得他又哼起了小曲儿。 “二喜叔,有啥好事儿,看把你美得。”在岔路口,范娃和小山看见了摇头晃脑口哼小曲的二喜,范娃忍不住问了一声。 二喜听见有人叫他,急忙捂住了胸前的毛主席像章。 “我知道,二喜叔今天又过年了。”小山说,“要不,哪有这么高兴。” “开会,开会,在公社开会。”二喜自豪地说。 “我说呢,嘴上咋油渍渍的。”范娃说。 二喜听范娃一说,下意识地抹了一下厚厚的嘴唇。“你俩跟我来,我有话跟你们说。”二喜声音很小,他看了看左右,样子很神秘。 范娃和小山见二喜神秘兮兮的样子,不知啥事儿,就跟二喜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啥事儿,二喜叔。”范娃问。 二喜又看了看左右,见没有人往这边来,很严肃地说:“今儿公社开会,成立了红卫兵总部,司令是衡来山。衡司令叫各大队成立红卫兵战斗队,要选根红苗正,家里穷,祖孙三代没有出过当官的人来当头头。衡司令叫我当,我想着我不识字,没有文化,年龄也大了,我思谋了半天,扳着指头数,挨着人头点,比来比去,我觉着咱大队就你俩最合适。你俩都识字,看得懂文件,认得到传单,还会写大字报,”二喜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白纸红字的传单递给范娃,“你看看,咋着搞,上头都写着哩。”二喜看了范娃一眼,“我想由你来当战斗队队长,小山当战斗队副队长。你俩看咋样?” 范娃受宠若惊。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立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进行革命大串连,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他都从收音机里听到过。他姐夫康光辰给他买的那个小玩艺里每天都在说这些。起初他听不懂,听的次数多了,也就听出点眉目了。他觉着这是城里人的事儿,跟他们无关。城里人不犁地,不种庄稼,不割草喂牛,不担土垫粪,吃了饭没事干,闲着难受,总得找点事儿做,要不,闲下病来还得住医院吃药打针,说不定还要开刀,那多疼。听说当年土改工作队说话结结巴巴的那个结壳子队长得了病,开了刀,把肠子割了一大节,换了一节狗肠子上去,后来说话就有点怪声怪气还夹带着狗腔狗调,有时冷不丁发出呜呜汪汪两声怪叫,听着吓死人。城里人大概都怕挨刀换狗肠子才生着法儿串连,生着法儿造反。农民天天忙着侍弄地里的庄稼,忙着背日头过山,哪有空儿去弄这些事儿。 “咱这里成立红卫兵战斗队弄啥?”范娃不解地问。 “说是叫拆庙砸神,揪斗坏人……”二喜这顿粉条熬肉总算没白吃,他还记住了司令衡来山最后强调的那几句话。 “我不当。”范娃说。 “我也不当。”小山说。 “那中。你们不当,有人想当。别人当了,整你们的时候,你们可别后悔。” “我们有啥叫别人整的?”范娃和小山几乎同时说道。 “那也说不准。你们说没有啥,要整你们的时候就可以找点啥。” 范娃和小山都瞪着眼睛,想不到二喜还思虑得这么远。 “别人当了,走东串西,吃香喝辣,不干活照挣工分。听衡司令说,平川市郊区的农民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开开会,喊喊口号,贴贴标语,举着小旗游行游行,工分比干活的人挣得还多。生产队给他们记的是政治工分。” “有这种事儿?”范娃还有些怀疑。 “这事儿大山也知道,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他。他总不会倒你们。” “那我再想想。”范娃说。 “中。你想好了跟我说,不能耽搁太久。要不,干脆这样,喝了汤我到你家里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二喜叔,俺家人多,说话不得劲儿。再说黑灯瞎火,你走着也不得劲儿,还是我跟小山到你家里去。” 二喜听范娃这样说,心里很不美,但也只好答应,“中,中。你娃子还想得周全。” 喝了汤,范娃跟小山一同来到二喜家里。赵大脚已经串门去了。二喜坐在那间低矮的茅草房里,面对昏黄的煤油灯,有滋有味地吸着旱烟。 “二喜叔。”范娃进门就甜甜地叫了一声。 “你俩来了,坐吧。”二喜很热情。 范娃和小山两人坐在一根扳凳上,面对二喜。 “大脚婶呢?”小山问。 “串门去了。”二喜说:“你俩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范娃说。 “干还是不干?” “干!”范娃回答得很干脆也很坚决。“既然二喜叔看得起咱,咱也决不给二喜叔丢脸。你说是不是小山?” 小山点点头。“范娃说得对,我也这么想。” “那中。不过,”二喜吸了一口烟,“还得通过贫下中农大会选举。” 范娃睁大了眼睛,直盯盯地看着二喜。 “我还以为是你指派。”范娃说:“还要经过贫下中农大会选举,你跟俺俩说了有球啥用?” “娃子,甭着急,只要你俩愿意干,选不选都是你俩。”二喜很有把握地说:“不信咱明天大会上见分晓。” 范娃和小山不知二喜葫芦里到底装的是啥药。 第二天晚上,刚喝罢汤,老榆树上的那块钢板被二喜敲得当当响。不大一会儿,全体贫下中农齐崭崭地坐到老榆树下。二喜拧亮马灯,挂在老榆树上。 二喜说:“今黑儿咱开个贫下中农大会,传达一下公社贫雇农代表大会的精神。公社贫雇农代表会上,宣布成立公社红卫兵总部,衡来山当总部司令,总部的任务是专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衡司令要求各大队成立红卫兵战斗队,专门抓革命斗坏人。今黑儿开会就是要落实上头的精神,选两个领头的,带领红卫兵专干这事儿。这两个人要根红苗正,还得识字儿。我扳着指头数了数,觉着范娃跟小山最合适,看大伙儿有没有意见。”二喜停止了讲话,按了一锅烟,点燃吸着,烟吸完了,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二喜问:“大伙儿有没有意见?”还是没有人开腔。“那就算通过。”二喜说。 就这样,范娃和小山当上了槐树沟红卫兵战斗队的头儿。 范娃和小山当了红卫兵战斗队的头儿,究竟该干些啥,咋干,他俩也是两眼一抹黑。那天,司令部开会,二喜带着他俩去了,满屋子里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的非常稚嫩,还是乳臭未干的毛娃娃。衡司令比他们大一些,看上去也就三十郎当岁。细高个儿,脸白白的,眼睛不大,样子很精明。说起来范娃和小山也都见过衡司令,他以前给公社书记赵书清当秘书,赵书记升到县上去了,反浮夸风时衡来山背了个官僚主义的名声,一直在公社当小干部,没有得到过重用。曾跃旗由助理员一下提为公社书记接了张光春的班,他心里很不平衡,现在造反了,一下就当上了司令,听大山说还是县委副书记赵书清点的将。衡司令跟他们说,要抓紧发展红卫兵队伍,抓紧开展工作。现在各地都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不能死气沉沉。前几天我跟县造反司令部到外地进行了参观,外地有很多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破“四旧”,斗坏人,贴大字报等,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咱们没经验,先学学别人。今天我给大家搞了个样板,等一下大家看看,好好学学,回去就照着干。衡来山说完了,把大家引到了戏楼前的空坝里。戏楼上牵了一副又宽又长的白色横标,上写斗大的黑字:“批判历史反革命分子王老虎大会”。“王老虎”三个字上还划了三个红叉叉。空坝里挤满了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没有凳子,人全都站着,一个挨一个,象看戏时一样。每逢运动,这里是固定的斗人场所。土改时,他们在这里看过斗争地主富农分子,“三反”“五反”时他们在这里看过斗争反革命分子,反右运动,他们在这里看过斗争右派分子,四清运动,他们在这里看过斗争贪污腐化分子……现在又在这里斗人,预示着又要开展运动了。衡来山戴着红袖套,上面印着三个黄色的大字:红卫兵。他手里拿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后来统称“红宝书”),很威严地走上了戏楼。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是衡来山讲话。主持人要求大家鼓掌,下面响起了下饺子似的巴掌声。衡来山翻开手中的小红本本,扯着嗓子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后,宣布“把历史反革命分子王老虎拉出来!”随即两个标形大汉一左一右挟持着一个瘦筋筋的老头子象掂小鸡一样掂上了台。老头子双手绑在背后,规规矩矩地跪在台上,衡来山宣布了老头子的罪状。说王老虎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连长,解放后一直不老实,总想变天。说到这里,衡来山拿出了一个揉得象麻叶的烂本子举在手上在空中挥了挥,说是王老虎记的变天账。衡来山说,象这种一直不死心的敌人枪毙一百回都不解恨……王老虎的罪状宣布完毕,接着又押上来一个胸前挂着大牌子的坏分子。衡来山说,这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道德败坏的流氓,从当土改工作队队长开始就一直乱搞妇女,被他糟蹋的妇女少说也有十几个。现在把这两个坏蛋交给大家批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衡来山的话音刚落,几个戴红袖套的小伙子就冲上了台,照着挂历史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那个老头子就是一顿拳脚,直打得王老虎哎哟哎哟直叫。接着把拳脚转向流氓分子。那人一见立即双膝跪地,浑身筛糠,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是狗、狗、狗……”台下一阵轰然大笑。“狗、狗肠子,打、打、打不得,一、一、一打,就、就、就断了。”这时台下的人才听明白,原来他是开过刀的,把他有毛病的肠子割了换成了狗肠子。 “管他狗肠子猪肠子,打!” “你搞妇女的时候咋没说你是狗、狗肠子,搞、搞、搞不得?”一个小伙子故意学着那人的腔调。 人群中又是一阵轰然大笑。 “打,打!” “打断他的狗肠子,打断他的狗球!” 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吼声。 一个小伙子飞起一脚把那人从台上踢下来,那人绊了个狗吃屎,在地上翻了个滚儿,手撑着地想站起来,不知是谁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那人一个扑爬,又栽了个嘴啃泥。接着你一脚他一脚,踢得那人缓不过气来。那人抱着头就地打滚,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伸出了愤怒的脚。那人成了过街老鼠。那人滚到范娃和小山跟前时,范娃咬着牙给了一脚,正好踢在那人的脸上,顿时,那人的嘴里流出了鲜血,一颗牙齿被鲜血裹着从嘴里吐出,鲜血染红了他的络腮胡。 范娃恶狠狠地说:“我叫你球痒!” 小山把脸扭向了一边。 “咱走吧。”过了一阵儿,小山轻轻地拉了一下范娃的衣角说。 “急啥,再看看。”范娃说。 回家的路上,二喜,范娃和小山都很少说话,他们都在回想着斗争大会上那一幕幕残烈的场面。 “你们知道那个流氓是谁?”二喜打破了沉默。 范娃说:“不知道。” 小山说:“我也不知道。” 二喜嘿嘿一笑,神秘地说:“他就是搞过何大流小妹子的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 范娃说:“早知道我该多踢他两脚。” 小山说:“早知道我也该踢他一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