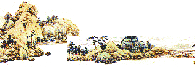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张光春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脸色很难看,没有一丝儿笑容,他被撤职了,据说他是全县浮夸的典型,在反浮夸风中被反下来了。在县上办学习班时,他跟赵副县长--原公社书记赵书清--编在一个组。赵副县长也是浮夸风浮起来的,也属于浮夸人物,也是被反的对象。但赵副县长毕竟多喝了几瓶墨水,肠肠肚肚五脏六肺都被墨水浸泡过,所以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检讨得很深刻,也就顺顺当当地过了关。在检讨会上,赵副县长说他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工作作风飘浮,深入调查不够,特别是听到张光春说他的试验田里一棵红薯结了一千多斤时,没有亲临现场实地察看,而只派了秘书前去,当时他头脑里想的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万万没想到张光春竟如此不可相信,秘书衡来山也偏听偏信,工作马虎,只听一面之词,不做实地调查,让张光春的千保证万保证保证是事实保证没虚假的一连串保证瞒过去了,当了小官僚。赵副县长这样一说,好象红薯卫星起根根发芽芽他一点也不知道,压根他就蒙在鼓里,是个典型的受骗上当者。结论是张光春搞浮夸风,衡来山犯官僚主义,他是充分相信群众而群众又不让他相信的上当受骗者。赵副县长检讨得很深刻,态度也很严肃,并历数了官僚主义的表现,深挖了官僚主义的危害,举着镢头刨根寻底找根源。赵副县长不愧是当官的料,话题一转又指出了几条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就这样,赵副县长就轻而易举地过了关,仍然当他的副县长,照样坐在他那把椅子上。 张光春可就有点惨了。他没念几天书,识不了几个字,检讨起来就不象赵副县长一套一套的那么深刻了。也多亏他的脑子好用,跟装了轴承一样,转得快。张光春听了赵副县长的检讨,心里很不是味道。赵副县长把事情说翻了个个儿,但他不敢开腔,只好认了,鼻子大了压扁嘴,他有啥法。一棵红薯结千斤是他搞试验时的想法,结果结了两箩筐筋,他并没有上报,不知赵副县长是听谁说的,就派了曾助理和衡秘书敲锣打鼓又是送红旗又是传达他的指示……硬把他这只鸭子赶上了架。现在鸭子在架上掉下来了,甩得半死不活,不怪赶鸭子的人,还怪起了鸭子,世上哪有这个道理?张光春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这样说,这样说了就是推卸责任,想把浮夸的责任推给上头,难着呢。自古以来,上头做错了事往下推,那是顺道,下坡路也好走。就象一块石头,用脚轻轻一蹬,顺着坡骨碌碌就下去了。同样是一块石头,从下往上推,推上坡道,那可就难了。费力是一回事儿,稍不小心石头还会从半道上滚下来,那可就不得了了,运气不好就要被压死,运气好了也难免受伤,弄你个缺胳膊少腿,这辈子也就彻底完了。这个道理,张光春再清楚不过了。小时候,他经常看屎壳螂推粪蛋,往下推轻轻松松,一点也不用劲,粪蛋滚得很快,往上推,憋足了劲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一不小心没把稳,粪蛋就骨碌碌滚到坡底下,屎壳螂还得重来。推责任跟屎壳螂推粪蛋蛋是一个理儿。张光春怕推不上去,反惹其祸,被粪蛋蛋压着,虽然压不死,但要弄一身臭味,还不如不推,留口气暖肚子,留口唾沫养牙齿。再说,他主动把责任承担了,赵副县长的乌纱帽保住了,交椅坐稳了,赵副县长也不会忘记他。留得青山在,还怕没紫烧。只要靠山不倒,东山再起是早晚的事儿。想到此,张光春的眼睛望着赵副县长,没想到赵副县长的眼睛也正看着他,他心里有点发慌,咂咂嘴,不知该咋说。赵副县长补充道,我们历来是讲实事求是的。犯了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自已看不到,认识不到,不敢或不承认错误,那就危险了。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就好了。”我们犯了错误的同志就象得了阑尾炎,切不可讳疾忌医,要主动请医生把阑尾割掉。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政策历来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决不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棒子打死……张光春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赵副县长已经给他定了调子,他按调子唱不会有错,如果不按调子唱,那他就成了傻瓜一个。于是张光春把浮夸的错误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好象那场浮夸风是他一个人刮起来的。张光春说是他亲口向赵副县长汇报的,说他放了一颗大卫星,一棵红薯结了一千多斤,他怕公社调查,事先就做了手脚……参观的人提出了疑问他还强词夺理,说一个娘生的娃还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高有低,一个母猪下的一窝猪娃也有公有母,有黑有白还有花的,一棵红薯为什么就不能结出红皮白心白皮红心的?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大跃进,离奇的事多了。柿子树上结香蕉,葫芦秧上结西瓜,兔子生小鸡,狐狸下狼娃……什么人间奇迹没有?参观的人不好跟他辩论也就胡弄过去了。张光春说,现在想起来,我那些话都是屁话,跟放屁没啥区别,放个屁也有点臭味儿,可我放的屁连点臭气也没有。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不知耽误了多少参观者的宝贵时间,也不知叫他们白化了多少路费,耽误了多少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栽培我的赵副县长……我请求组织请求领导给我处分。张光春说得眼泪花花几次哽咽,好象那漫天的浮夸风是他偷了牛魔王的芭蕉扇扇起来的。张光春请求组织请求领导给他处分,组织和领导都很大方,满足了他的请求。大领导撤去了他这个小领导的职务,大领导还是大领导,他这个小领导就变成了老百姓。据说在那场反浮夸风中,张光春是神佑县唯一被摘了乌纱帽的官员,不过他那顶乌纱帽确实是浮夸风吹来的,浮夸风被反了,摘去他的乌纱帽也是合情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了。那些大当官的,原本就是当官的,就象赵副县长,头上原本就有乌纱帽,只不过在浮夸风中被吹长了吹大了,最多再给它缩缩水,使其复归原状。但就是找不到缩水的人。没人给缩水也就算了,赵副县长也就照样戴着他那顶被浮夸风吹大的膨胀了的乌纱帽。用赵副县长的话说,反浮夸风给他洗了洗脑筋,他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其实也未必。 张光春背着铺盖卷回来了,从行装上看,他并没有失去什么,去上任时背的这个铺盖卷,如今回来了,也是背的这个铺盖卷,一根线也没少。他本来就是农民,那场风把他刮上去了,他象地上的一根鸡毛,被突如其来的大风卷到了天上,不由自主地在空中飘啊飘啊,那种感觉确实很美,什么也看到了,什么也尝到了,要说不好的,就是自己不能把握自己,失去了自主权。现在,风驻了,他从空中落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鸡毛能上天也能落地,这并不在鸡毛本身有那种本事,关键是要有一种动力--风。风没有了,鸡毛要是不落下来那才真正成了怪事。张光春觉着不当公社书记也没啥,重要的是名声不好听,所以心里还是很难受。他进村的时候,最怕的事儿是遇见人,但他还是遇见了。好在那些人没有给他难看的脸色,也没说讥讽的话语,都是平平常常一句话,你回来?好象他不是在外面做官犯了错误被削职为民逐回了家,而是到县城赶了一个集。张光源看见了他,老远老远就走了过来,接过他背上的铺盖卷,把他送回了家。 张光源是大队长。 张光春回来后,闷闷不乐。昨天还在天上,今天就落到了地上,不管咋说,天上总是仙境,地上总是凡间,地上再好也是不能与天上相比的。张光春很不习惯,又觉着有些丢人,所以成天闷在家里,不愿见人。他吃了饭睡觉,睡了觉吃饭,要不就一个人干坐着吸闷烟。他很少跟他的老婆说话,也很少理儿子老闷。 那天,村里的人都下地去了,张光春的老婆和儿子老闷也扛着家伙走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吸了两袋烟,觉着心里起急,老在家里坐着也不是办法,日子久了会闷下病来。他决定趁人都下地了,先在村里转转,散散心,解解烦。 张光春刚走出大门,看见村东头走过来一个人,披头散发,敞胸露怀,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枕头,边走边唠叨着,并使劲把油腻的枕头往胸脯上按。张光春感到奇怪,他认真地打量着离他不远的那个人。那人越来越近了,张光春不觉打了个寒颤。他想退回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啊啊,娃儿乖乖,娃儿吃奶奶。啊啊,娃儿乖乖,娃儿睡觉了……”茶花边拍着怀里的枕头边哼着小曲儿走到了张光春的面前。 张光春一见,眼里忍不住涌出了泪水。那个美丽得光彩照人活泼得象只小喜鹊的茶花咋变成了这样?昔日的茶花哪里去了?他用泪眼去搜寻,在面前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身上去寻找过去的茶花的影子,但他什么也没找到。他听他老婆说过,茶花被畜牲何大流强奸后疯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被糟蹋了的茶花会变成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特别是她那神圣的令女人引以自豪也令男人垂涎三尺而想入非非的神秘的乳房,那时是多么美丽多么白净啊,现在却弄得又黑又脏象在污水里浸泡过的茄子。张光春的眼泪落下来了,他忍不住轻轻地喊了一声“茶花。”他的声音很小,有些颤抖,但却充满了感情。 茶花瞪着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张光春,惊疑地问:“你是谁?别吵,乖乖睡觉了。啊啊……” “茶花!”张光春又叫了一声,语气加重了。 茶花仔细一看,哈哈大笑。 “哦,是你回来了,我还没看见。乖乖,快,睁开眼,别睡了,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你爹回来了,你爹他回来了!” 茶花把紧紧抱在怀里的黑不里几的枕头往张光春面前一递,又蹦又笑。 “快,快呀,快抱一下你的小宝宝,他可想你了!” 张光春见状,不知所措。他想逃跑,但又害怕。万一他一跑,茶花抱着枕头跟在他屁股后头紧追不舍,那又怎么办?他只有硬着头皮站在那儿,嘴里不住地叫着“茶花,茶花!”。张光春把茶花塞到他手里的脏兮兮的枕头一推说:“你醒醒,好好看看,这不是乖乖,也不是宝宝,这是枕头,枕头,烂枕头!” “你这个没良心的,”茶花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出门才几天,连我们的小乖乖都不认了。明明是我们的小乖乖,你说是枕头,没良心,没良心!我咋找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茶花生气了,一把把枕头搂在怀里,抱得更紧。“啊,啊,乖乖,别哭别哭,吃奶奶。爹不要你娘要你。啊,啊,别哭,别哭……” 正当张光春无法脱身的时候,茶花娘来了。她瘦了,老了,头发花白了,脸皮松弛了,脸上起了很多皱纹。还有那一双会说话的灿烂得摄人魂魄的大眼睛,如今变成了两个死水般的深潭,静静地,静得可怕,静得吓人,极其深沉而无一丝活泛。两只黑葡萄似的眼仁,颜色已经变淡,淡得就象一瓶墨水中掺了一缸凉水,又象一件黑色的衣裳穿得过久而洗涮得褪去了颜色,变成灰扑扑的了。 “你回来了。”王彩珠跟张光春打着招呼,声音平淡,听起来凉巴巴的如井水。 “回来了。”张光春问:“茶花,她……” “憨了。”王彩珠说:“走,别跟你叔没大没小的。”王彩珠拉着茶花,眼睛望着张光春,“她叔,你别理她,她憨了。” 茶花使劲甩开她娘的手。 “我不走。他没良心,出门几天就把我们忘了,不要俺娘儿俩了。娘,你看,小乖乖多可怜。” “净说憨话。走,回家。”王彩珠生拉活扯地把茶花拉走了。 茶花一步一回头,望着张光春。 “你可不能没有良心,不要我可以,可不能不要小乖乖,娃儿没爹,长大要受气……” 无论茶花说什么,村里的人都当做笑话。茶花是疯子,茶花的嘴就象没关的门,想说啥说啥,疯子的话谁会相信?所以也就没有人把茶花被强奸的事儿与张光春往一起牵扯。何况那时张光春是公社书记,没在村里,而且强奸犯何大流已被公安局关进了监狱。然而,张光春听着茶花的话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起初,他害怕,后来茶花娘一再说闺女憨了说的是憨话,他也就放心了,不再害怕了。但不管咋说,茶花的话对他来说就象一块巨石投入水潭,在他心里激起了波涛,溅起了浪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