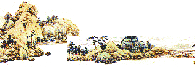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岁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记号:21-2001-A-(0656)-0115
|
||||||
惠贤的病好了。 食堂还是老样子。一天三顿清汤寡水。 张光源跟妻子惠贤说:“咱退食堂吧。” 惠贤说:“那不又成了单干?” 张光源说:“管他单干不单干,只要能吃饱肚子。” 惠贤说:“上头准不准?” 张光源说:“入食堂时上头就说过,入退自愿。” 惠贤说:“你可弄清楚,甭再戴高帽子,老丢人。” 张光源说:“有啥丢人的,戴高子总比饿着强。” 惠贤说:“我愿意饿着也不愿意丢那人。” 张光源说:“怕啥,外村都有人退了。” 惠贤问:“戴没戴高帽子?” 张光源说:“没有戴。” 惠贤问:“上头说啥没说啥?” 张光源说:“没说啥。” 惠贤说:“那中,咱退。” 张光源退食堂的事象在死气沉沉的小山村里丢了一颗炸弹,炸去了死气,炸碎了沉闷,炸出了生机,引起了轰动。几个月没有烧过的冷灶燃起了火苗,几个月没有冒过烟的灶房冒出了一缕淡淡的青烟。不少社员望着张光源家那袅袅上升的饮烟,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那尘封已久的灶房,扫起了灶台上厚厚的灰尘。 张光源的举动,何大流非常气愤,他跟社员们说,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单干。张光源走的是单干的道路,那是一条黑道,是没有前途的路,大家不能跟他学。他想开社员大会斗争张光源,请示公社,公社没答应。公社曾助理说,中央有精神,社员可以自愿入食堂也可以自愿退食堂。有的地方公共食堂已经解散了,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食堂可以成立也可以解散。何大流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食堂一散,他再也无法做到他想吃啥就吃啥,他说吃啥就吃啥,他说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他的胃就不是全村人的胃而变成自己的胃了,他再也不能开小灶吃偏食了……想到这些,何大流对张光源是气恨交加,要不是上头有精神,他一定要象张光春那样给张光源戴上一顶破坏公共食堂的高帽子,叫他游街,叫他丢人。面对越来越多要求退出食堂的社员,何大流欲阻不能,欲止不敢,因为上头的权力远远大过他的权力。他不解的是,办食堂是上头叫办的,解散食堂也是上头叫解散的。何大流说,上头的事也没个准头,说不定今天解散了明天又叫你办。 自从张光源退出食堂后,那些暗暗打扫灶台一直观望的社员们见张光源没有挨批斗,也没有戴高帽子,于是就步张光源的后尘,于是就纷纷退出了食堂,于是各家各户的灶房里都冒出了青烟。几个月来只有一个烟囱冒烟的山村出现了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壮观景象。 开春了。张光源扛着镢头上山开荒,这是刚刚传达的上头的政策,允许社员开小片荒地,自种自收,三年不变。社员们来劲儿了,象张光源一样扛着镢头奔上山坡,蚂蚁般地啃着未曾耕种过的处女地。那劲头就象当年王震将军带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一样。 食堂越来越冷清了,昔日的热闹景象已成昨日黄花。坚持在食堂吃饭的只有几个懒得连自己身上的虱子都不愿逮的光棍汉。何大流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要在往常,只要他站在老榆树下,拿起钟锤当当当敲响那块钢板,村里的人就会端着锅端着碗端着盆端着盛饭的家伙在食堂门前排起长龙,他拿着瓢象慈善机构舍饭一样,一瓢一瓢地给社员们分饭。那些想要稠一点的,想多要两疙瘩红薯的,想叫饭瓢舀满一点的,无不给他送上讨好的笑脸。他也养成了习惯,每次下瓢的时候,总要先看看递上盛饭家伙的那个人的脸,然后决定舀干舀稀舀多舀少下瓢深浅。茶花来领饭,何大流最喜欢,虽然茶花不象别人递上笑脸,甚至有时还恨他一眼,但何大流看着心里也是美的。茶花笑也好恨也罢,何大流总是选干的舀。有一回,何大流只顾看茶花那圆圆的脸,把一瓢稀饭倒在了茶花的盆外,浅了茶花一身。何大流没有少给茶花家好处,可以说在食堂里得到好处最多的除了他何大流和张光春家外,就是茶花家了。但他万万没想到,食堂的最大受益者--茶花家--居然也跟在张光源的屁股后头跑,退出了食堂。茶花不来排队领饭了,何大流无法看到茶花,心里很难受,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 何大流又敲响了吊在老榆树上的钢板,到食堂领饭的人稀稀拉拉地来了。净是老的,有病的,还有几个光棍汉。何大流掂着瓢,抬眼一看,那一张张脸无一不是脸色黝黑,皮肤粗糙,表情麻木,近乎痴呆。特别是有几个年纪大的,脸枯抽着象蛋(睾丸)皮一样,深深的皱纹里填满了黑得令人厌恶的一看就要发呕的灰尘。何大流把手中的权力--饭瓢--往伴伙夫面前一递说,从今天起由你掌瓢。 何大流也想退食堂了,他发愁的是他要退了,这食堂谁来管。上头的政策是入食堂自愿退食堂也自愿,可这些人不愿退,他总不能站在老榆树下一敲钢板吆喝一声,喂!食堂解散啦!就这样结束食堂的生命。他怕光棍汉们的到公社告他。何大流想退而又不敢退,他是村里的头儿,他怕挨上头的批评。转而他恨起这些人来了。你们咋不学张光源,跟着他飞了不就算球了,我也可以自由自在。 张光源退食堂没几天,退食堂的社员就占了一大半。很多人早就想退,但又不愿当出头鸟,怕挨枪子儿。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张光源带头退了,他当了鸟头,先飞了,一大群鸟分裂了,有一多半跟在他的后头扑楞着翅膀紧追不舍,追上他的都是些羽毛美丽鸣声婉转的对对鸟,而且带走了羽毛刚丰光彩照人活泼可爱的小鸟。鸟群里剩下的尽是些羽毛秃败形单影只的无依无靠者。何大流也是一只美丽的鸟,跟他们在一起无法合群,无话可说,憋着一肚子气而又无处发火,他觉着这样生活着毫无情趣,而且有些窝囊。所以他才放弃了手中的权力,把他一直不愿丢的饭瓢塞给了胖伙夫。 何大流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小姜猪也不看他的脸色就泼水似的说了一串难听话。 “我叫你早点退,你偏不退,舍不得那些骚货,现在骚货退了,看你还骚哪个?” 小姜猪还是老样子,只是较前稍瘦了些。自从为何大流生了娃子后自认为有功,在何大流面前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后来娃子死了,她大声说话的习惯一直没变,说起话来仍然一句是一句,干脆利落,象小镢头挖地铮铮有声。 何大流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发,也找不到地方发,一直忍着,差点把肚皮憋破。此时小姜猪指桑骂槐,借机发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自从小姜猪生了娃子后,恃功居傲,多次指责他说,你那眼睛是专为那骚货长的,要是一天没看见,就象八辈子没吃饭饿得睡不着。吃食堂了,你的眼睛又从老骚货转向小妖精,不过那小妖精比黄脸婆水灵,你看着心里受活。小姜猪越说越气,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难听。何大流被揭了痛处,几次想打小姜猪,但每次都是高高抬起手,轻轻又放下,他不忍心,他觉得小姜猪不管咋说给他生过娃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娃子没养活也不能全怪她,所以何大流没有打小姜猪。对小姜猪的话,何大流想,这狗日的未必是孙悟空,钻进了老子的肚里,要不她咋啥都知道?罢罢罢,老子现在不理你,等你狗日的从老子肚里出来时再咬你。小姜猪毕竟不是何大流肚子里的回食虫,何大流心里究竟想的啥,小姜猪也弄不清楚,她只知道何大流心虚了,怕她了,所以她接着数落。你一天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日了老的想日小的,再不收心,小心雷劈。何大流终于忍受不了小姜猪这恶毒的咒骂,只听他牙齿咯嘣响了一声,啪啪,两个响亮的耳光落在了小姜猪的脸上。恶狠狠地吐出了一句话,我叫你这张喷粪的嘴! 小姜猪的嘴角出血了,小姜猪睡在地上打滚了,小姜猪哭喊连天,小姜猪骂声震地……何大流走上前照着小姜猪圆滚滚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娘那个X!看你那副雕样子,长球得跟狗熊一样还看不惯老子。球本事没有,连个娃子也养不活。实话跟你说,你要不想跟我过趁早滚蛋,你看老子离了你能不能活? 何大流普天盖地一顿臭骂,小姜猪越发哭得痛了,她倒不是怕卷铺盖滚蛋,他想起了她那死去的儿子。她儿子长得很乖,样子活脱脱的象何大流。他的出世如沾合剂一样把这个有着深深裂痕即将破裂的家庭沾在了一起。自从有了娃子,何大流往外跑的时间少了,也很少去找那个老骚货了,对她也不象以前那么冷淡了,吃了饭,何大流总要抱着娃子亲两口,在村里悠一悠。随着儿子的长大,家里也有了笑声,这是儿子给家里带来的欢乐。正当他们欢欢喜喜过日子的时候,儿子生病了。吃了几副药,打了几天针,病总不见轻。小姜猪说干脆把火燕请来给儿子扎扎火针,何大流说儿子老小,怕挨不起火针,再说儿子也老疼。何大流跑了一百多里路从平川市郊请来一个老中医,老中医在家里住了几天还是没有保住儿子的性命。儿子死了,小姜猪哭得死去活来,她怪那个老中医,枉活了七十多岁,枉长了一脸的白胡子,啥药引子不会用,偏偏要用麻雀胆?麻雀都被打死光了,麻雀胆往哪里去找?何大流在山坡上撒了一大片小米和麦子,想把麻雀引来,可是他在那里守了一天一夜,连饭也没吃,还是没有见到一只麻雀的影子。何大流彻底失望了,他在心里暗暗怪二喜,麻雀是挖了你的祖坟还是把你的娃子推到井里了,你领着娃子们拿着棍子撵,敲锣打鼓地吓,放枪放炮地打,把它们消灭得一只不剩。何大流怪了一阵儿,转念一想,怪二喜有球啥用,二喜领着娃子们打麻雀还不是你何大流的分派,你何大流每天还要亲自验收他们剪下来的麻雀腿,还大会小会地表扬,说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把麻雀撵得满天飞,麻雀飞不动了,就从天上掉下来,象是天上下下来的肉疙瘩,既省了枪子儿又省了火药……这能怪二喜?但也不能怪自己。麻雀是找不到了,莫说是他何大流的儿子要死了,现在就是省长县长的儿子要死了,这种药引子也找不到。找不到麻雀胆,儿子的命就无法救了,小姜猪和何大流流着眼泪求医生给换换药引子,医生说,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断准病下不准药,等于不下。给你儿子下的药是对了症的,药引子换了也就对不了症,对不了症也就治不了病。你儿子的病非这药引子不可。小姜猪一听哭得更痛,转而怪起何大流来,都是你们这些吃了饭没事干的东西害了我的儿子!麻雀是吃你了喝你了还是碍你啥事儿了,活得好好的你们派人去打,这到底是为啥?现在娃子要死了,这不是咱遭了报应……小姜猪看着就要断气的儿子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哭诉着,何大流听着心里十分难受,但他还是说,你怪我我怪谁,你以为我想去打那麻雀,那是上头布置的,我敢不执行?小姜猪想了想,确实不能光怪她的男人,于是停止了诉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现在小姜猪想起儿子的惨死哭得更加伤心。何大流以为逮住了小姜猪的短处,接着数落。 “你知道老子不想退食堂,老子现在是有心无胆不敢退。实话跟你说,老子要不是大队长早他妈的退了,还能等到现在,还能等到你说!” 何大流说了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茶花家没退,他根本没想过退,茶花家退了,他才产生了想退的念头,并不是早就想退。虽然何大流的话并不全是真的,但小姜猪听着心里舒坦,何大流不是留恋那一老一小两个骚货才不退的,而是因为他是大队长不能先退。小姜猪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已男人的难处,话骂得太狠了,太重了,太难听了,他男人是受了委屈才发火才打她的。小姜猪似乎明白了,她挨打不能怪她男人而只能怪她自己。道理明白了,小姜猪也就停止了嚎啕。 “哪咱啥时退?”小姜猪问。 “等食堂解散。”何大流似乎有些无奈。 没过几天,食堂解散了。何大流说这是上头的政策。 一家一户过日子,再难自己都会想办法。各家各户开的小片荒地星星点点布满山坡,倭瓜秧子造出的片片绿地尤如沙漠中的绿洲又象海洋中的小岛。为了尽快解除饥饿的威胁,小片荒地上都是种的倭瓜,这种植物只要不缺水不缺肥,长得很快,瓜没结出,花先开放,那美似金铃的黄花首先给人们送来了一道好菜。人们望着那黄色的花朵,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喜色。 小片荒地暂时解决了人们的饥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