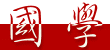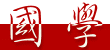康广仁传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
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
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
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
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踰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
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
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
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君曰:“今日在我
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
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
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
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
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
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
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
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
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
“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
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
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
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
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
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
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
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
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
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
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
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
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
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
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
“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
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
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
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
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
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
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
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
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
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
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
亦何伤!
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
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
伤哉?”程曰:
“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
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
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
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
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
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
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
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
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
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
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
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
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
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
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
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管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
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 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
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 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
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
传于后。君既弃浙官,今年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
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 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
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 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
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杨深秀传
杨君字漪邨,又号孴孴子,山西闻喜县人也。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自十三经、史、汉、通鉴、管、荀、庄、墨、老、列、韩、吕诸子,乃至《说
文》、《玉篇》、《水经注》,旁及佛典,皆能举其辞。又能鉤玄提要,独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讲宋明义理之学,以气节自厉,岧嶢独出,为山西儒宗。其为举人,负士
林重望。光绪八年,张公之洞巡抚山西,创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 特聘君为院长,以矜式多士。光绪十五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
三年十二月,授出东道监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时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旧学,而不知其达时务,至是,共惊服之。
君与康君广仁交最厚。康君专持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日夜谋此举。四月初间,君乃先抗疏请更文体,凡试事仍以四书、五经命题,而篇中当纵论时事,不得仍破承八
股之式。
盖八股之弊,积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扫,故以渐而进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议行。时皇上锐意维新,而守旧大臣盈廷,竞思阻挠,君谓国是不定,则人心不知所响,如泛
舟中流,而不知所济,乃与徐公致靖先后上疏,请定国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遂下,天下志士喝喝向风矣。
初请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议,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庸谬昏横,辄欲驳斥,又于经济
科一事,多为阻挠。时八股尚未废,许自恃为礼部长官,专务遏抑斯举。君于是与御史
宋伯鲁合疏劾之,有诏命许应骙自陈,于是旧党始恶君,力与为难矣。
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城,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后,虑国危,文君门下有某人者,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祠,竟夕语君宫中隐
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长麟去官之故乎?长麟以上名虽亲政,实则受制于后,请上独揽大权,曰: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
其言可谓独得大义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见澍贝勒仅一袴蔽
体,上身无衣,时方正月祈寒,拥炉战栗,吾怜之,赏钱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孙如此,
盖为上示戒,故上见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
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
“吾少尝慕游侠,能踰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壮其言而虑其难。时文数访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请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日腾谤于朝,以求自解。犹虑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开保国会,为守旧大众所恶,因附会劾之,以媚于众。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
文梯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杨,且责文之诬罔,令还原衙门行走。于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报,连上书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请派亲王贝勒宗室游历各国,遣学生留学日本,皆蒙采纳施行。又请上面试京朝官,日轮二十人,择通才召见试用,而罢其
罢老庸愚不通时务者,于是朝士大怨。
然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
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旧党与之为难,交章弹劾之,其
诬词不可听闻。君独抗疏为剖辨,于是奉旨奖励陈,而严责旧党,湖南浮议稍息,陈乃得复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陈国难,请西
后撤帘归政,遂就缚。狱中有诗十数章,怆怀圣君,睠念外患,忠诚之气,溢于言表,论者以为虽前明方正学,杨椒山之烈,不是过也。
君持躬廉正,取与之间,虽一介不苟。官御史时,家赤贫,衣食或不继,时惟佣诗
文以自给,不稍改其初。居京师二十年,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坚苦刻厉,高节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焉。子韍田,字米裳,举人,能世其学,通天算格致,厉节笃行,有父风。
论曰: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彼逆后贼臣,包藏祸心,蓄志既久,先生岂不知
之?垂帘之诏既下,祸变已成,非空言所能补救,先生岂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
抗疏谔谔,为请撤帘之评论,斯岂非孔子所谓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变,天地反常,
日月异色,内外大小臣僚,以数万计,下心低首,忍气吞声,无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
而先生乃从容慷慨,以明大义于天下,宁不知其无益哉?以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尔
也。呜呼!荆卿虽醢,暴嬴之魄已寒;敬业虽夷,牝朝之数随尽。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
岂计成败乎?
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
杨锐传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张公之洞
督学四川,君时尚少,为张所拔识,因受业为弟子。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光绪十五年,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张出任封疆将二十年,而君供职京僚,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
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君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自乙未和议以后,乃益慷慨谈时务。时南海先生在京
师,过从极密。南海与志士倡设强学会,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杨崇伊承某 大臣意旨,劾强学会,遂下诏封禁,会中志士愤激,连署争之。向例,凡连署之书,其
名次皆以衙门为先后,君官内阁,当首署,而会员中,F君FF亦同官内阁,争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门为前辈。”乃先焉。当时会既被禁,京师哗然,谓将兴大狱,君乃奋
然率诸人以抗争之,亦可谓不畏强御矣。
丁酉冬,胶变起,康先生至京师上书。君乃日与谋,极称之于给事高君燮曾。高君
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国会于京师,君与刘君光第皆会员,又自开蜀学会于四川会馆,集赀钜万,规模仓卒而成,以此益为守旧者所嫉忌。张公之
洞累欲荐之,以门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抚陈公宝箴荐之,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刘、林同参预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硃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
无得瞻顾,凡有奏摺皆经四卿阅视,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于是军机大臣嫉妒之,势 不两立。七月下旬,宫中变态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见君,赐以衣带诏,乃言位将不保,
命康先生与四人同设法救护者也。
君久居京师,最审朝局,又习闻宫廷之事,知二十年来之国脉,皆斲丧于西后之手,
愤懑不自禁,义气形于词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维峻、学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联英,因忤后落职者也;安者,曾疏请西后勿揽政权,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请皇上自收大权,因忤后革职驱逐者也。君习与诸君游,宗旨最合,久
有裁抑吕、武之志。至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遂被逮授命。君博学,长于诗,尝辑 注《晋书》,极闳博,于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
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君子重之。
论曰:叔峤之接人发论,循循若处子,至其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以视平日口谈忠孝,动称义愤,一遇君父朋友之难,则反眼下石者何
如哉?
林旭传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瓌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乙未割辽、台,君方应试春官,乃发愤上书,请拒和议,盖意志已倜傥矣。既而官内阁中书,盖闻南海之学,慕之,谒南海,闻所论政治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
先是胶警初报,事变綦急,南海先生以为振厉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而杨君锐实为蜀学会之领袖。君遍谒乡先达鼓之,一日而成,以月
初十日开大会于福建会馆,闽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及开保国会,君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
初,荣禄尝为福州将军,雅好闽人,而君又沈文肃公之孙婿,才名藉甚,故荣颇欲
罗致之。五月,荣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请命于南海,问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
也。”于是君乃决就荣聘,已而举应经济特科。会少詹王锡蕃荐君于朝,七月召见,上 命将奏对之语,再誊出呈览,盖因君操闽语,上不尽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称述
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 新政。十日之中,所陈奏甚多,上谕多由君所拟。
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呼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
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 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及变起,同被捕,十三日斩于市。临刑呼监斩吏问罪名,
吏不顾而去,君神色不稍变云。著有《晚翠轩诗集》若干卷,长短句及杂文若干卷。妻 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入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
乃仰药以殉论曰:暾谷少余一岁,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长于诗词,喜吟咏,余规之曰: “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君则幡然戒诗,尽割舍旧习,从南海治义理经世之学,岂所谓从善如不及邪?荣禄之爱暾谷,罗致暾谷,致敬尽礼,一旦则悍然不问
其罪否,骈而戮之,彼豺狼者岂复有爱根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杯酒,暮白刃, 虽父母兄弟犹且不顾,他又何怪!
刘光第传
刘君字裴村,四川富顺县人。性端重敦笃,不苟言笑,志节崭然。博学能文诗,善书法。诗在韩、杜之间,书学鲁公,气骨森竦,严整肖其为人。弱冠后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光绪二十年,以亲丧去官,教授乡里,提倡实学,蜀人化之。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及南海先生开保国会,君翩然来为会员。七月,以陈公宝箴荐,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初,君与谭君尚未识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则大相契。谭君以为京师所见高节笃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
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罗织,谓为叛逆。皇上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摺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君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
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独为君子也。”于是谭君益大服君。
变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狱,未经讯鞫。故事,提犯自东门出则宥,出西门则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门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谙囚狱故事,太息曰:“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君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贫,坚苦刻厉,诗文甚富,就义后,未知其稿所在。
论曰:“裴村之识余,介口口口先生。口口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
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
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与裴村未稔,故不能详
记行谊,虽然,荦荦数端,亦可以见其概矣。
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
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
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
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
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
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
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
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
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
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
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 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 无异入山。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口口口口口口口
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 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为学堂教习,召口口口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
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
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
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人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康、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捧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
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 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联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
法筹救”之语,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
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 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
“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
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
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 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今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
“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
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 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
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
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 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
死期耳!
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
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
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
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
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子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
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
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
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图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
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及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
余将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主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棱棱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国,为中国女学会创办董事。
论曰: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自唐、宋以 后,呫毕小儒,徇其一孔之论,以谤佛毁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
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
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
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
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 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
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
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