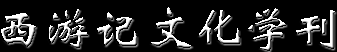 (第一辑)
(第一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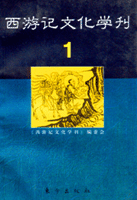
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李安纲
自从笔者在《山西大学学报》(1993,3)和《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东方出版社,1995,10)中提出来吴承恩不是《西游记》小说作者的论点,并且在《新评新校西游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7)中首次采用了“无名氏”的说法,得到了海内外数百家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的转载和披露,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有些学者仍然认为,只要是鲁迅和胡适二位先生论证了的,就是正确的,是不能够随便去掉吴承恩的署名权的。
我们以为,鲁迅与胡适二位先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真理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谁,都可能犯错误;不管是谁,都可能说得对。说得对,我们就该听取;说得不对,我们就该否定。否定了谬误,就会前进,也是对我们的先辈的爱护。本着这样的目的,笔者再次重申和强调以下的观点,以供广大读者参考和判断。
作者的问题,尽管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于《西游记》小说的研究,但由于“知人论世”的观点,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主题。如果作者是吴承恩,那么小说的主题就一定会是幽默滑稽。因为吴承恩是个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懂佛学”、“没有看过佛经”的人,而且只会插科打诨的无聊文人而已,所以小说肯定是与佛学和道学无关。
然而,任何一个读者只要认真地去加以研究,或者是实事求是地说句真话,都不能否定小说与佛道,尤其是后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对作者的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了。章培恒、杨秉祺、徐朔方、中野美代子等海内外的学者们都有过论述,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更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主题思想、文化载体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考证和对比而已。在这里我想强调几个问题。我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我得拿出足够充分的证据来;同样,要说吴承恩是小说的作者,也得拿出过硬的证据来。因为署吴承恩为作者,仅仅是从鲁迅与胡适开始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个前提条件。
其一,说吴承恩是作者,其唯一的根据是明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中的《淮贤文目》的记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里明明写着“文目”,是诗词文章或诗文集子的目录,没有说是书目啊!《射阳集》是部诗文集,《春秋列传序》自然是一篇简短的序言文章而已。那么,紧列其后的《西游记》,怎么能够会是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百回本小说呢!
照这样的观点,只要是写过《西游记》的,都可以去争夺那小说的署名权。那么,与吴承恩同时的杭州人张翰,也曾经写过一篇《西游记》,自然也应该成为小说的作者了。可为什么大家不把他当做作者呢?吴玉扌晋、阮葵生与鲁迅、胡适等前辈在否定了丘处机作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之后,又犯下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不论它的性质是什么,只要是名字叫做《西游记》,那就一定是百回本小说。
还有的学者,一定要我找出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文章来,然后再来去掉他作为小说的作者的署名权。但是,问题却不在这里。如果说,吴承恩的署名权是从小说一开始流传就具有了的话,那么,我要否定他的著作权,就必须找出他所著的那一篇文章来。鲁迅等人否定了丘处机作为小说作者的署名权,原因是他们声称自己发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但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丘处机的徒弟李志常等人著的,并不是丘处机自己所撰著的,所以他们还没有找到一部属于丘处机自己所著的《西游记》。但是学界却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从而否定了丘处机的作者署名权。那么,如果我们讲得对,有事实依据,为什么还非要我们找出吴承恩的《西游记》文章来,才会同意我们去掉他的署名权呢!找出吴承恩的《西游记》文章,那是研究吴承恩这个人物的学者们的事情,并不是《西游记》学者们应该做的。
其二,《淮安府志》的《近代文苑》中说吴承恩是:“复善谐剧,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前人包括鲁迅先生等,都认为“杂记”即是《西游记》小说。果真如此,那么“数种”该如何理解呢?是否吴承恩除了《西游记》小说之外,还著有其他洋洋数十万言的小说,也即杂记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呢?如果没有,那么这里就牵涉到了“杂记”的定义如何理解的问题了。
刘知几的《史通·杂述》云:“史氏流别,其流十焉。……八曰杂记。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里讲得非常明白了,“杂记”是指的如以上诸人所著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并不是百回本的长篇白话小说。
根据吴氏自己的《〈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情物,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由此可见,《淮安府志·近代文苑》中所谓的“杂记”,只能是刘知几所说的“史氏流别”中的文言志怪小说,也就是吴承恩所著的文言志怪小说《禹鼎志》。其中所记载的“十数事”,也就是十数种杂记。其中的几篇,在当时比较有些影响,即是所谓的“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也为他赢得了一些名声。
吴承恩是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要弄清楚《淮安府志》上所说的“杂记”的定义和性质是什么。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不是杂记呢?从刘知几的《史通》上看显然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了,鲁迅、胡适等人的“吴承恩是小说作者”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三,根据上述吴承恩所著的《禹鼎志序》中他自己的说法,他所喜爱的是牛僧儒的《玄怪录》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玄怪录》又名《幽怪录》,十卷,已佚,今《太平广记》中尚存三十余篇,内容多是记载玄奇鬼怪的事,文辞工丽;《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或记录秘藏,或叙述异事,以及仙佛人鬼、山川异物等。
以上这些文言志怪短篇小说发展到后来,就成了《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等,与白话神魔或者文化小说的《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又怎么能够睁着眼睛把他所喜爱的这些志怪短篇小说与那白话长篇小说的《西游记》等同呢!我们硬要把他所喜爱的文言短篇小说说成是长篇的白话小说,真不知道那吴承恩泉下有知,是高兴还是恼火!
他不仅爱好,而且还一直想写一部这样的“书”来“对之”。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他的目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写上一部文言志怪短篇小说,而且没有一点意思要写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从其中的“幼年”、“比长”、“迨于既壮”三个时间的术语看,可知他这个时候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在搜罗着奇闻异事。而“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的时候,至少也要到四十来岁了吧。
但到后来,他把搜罗到的奇怪事情却“转懒转忘”,甚至“胸中贮者消尽”。这也应该是五六十岁以后的事情了。决不可能一个正常的人,四十来岁记下的东西,当时就忘了的。况且,他所搜罗的那些奇闻异事不等写出来的时候,都快忘光了,只剩下了十来个怪异的故事。后来,整天与懒惰战斗,终于赢得了胜利,才写出来了《禹鼎志》。“尚存”的“磊块”已消,完成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那么,他也就不会有创作什么长篇白话小说《西游记》的动机和时间了。再说,《西游记》中所写的和表现的并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的精髓,与吴承恩所写的《禹鼎志》有着天壤的差别。
其四,有的学者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作者的根据,是因为小说中多用的是淮安方言。而吴承恩正好是淮安人,依此就可以确定他是小说的作者。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方言能不能作为判断这部文学作品所属权的依据呢?科学地说,即使是小说中全部用的是淮安方言,这也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是绝对不能当做判定作者的依据的。
随着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交流,方言的障碍越来越小,大家基本上都奉行了一种官话的系统。比如《切韵》和《广韵》等,都是当时基本上通行的一种官话系统。社会上流行的许多词语都是大家所能懂的,否则就无法进行沟通了。我们所谓的方言,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词汇,一个是方音。词汇的分别的确是越来越小,而方音的变化并不见得很大。不过纯粹用方音来写的小说,并不是多见的。况且,当时并没有什么记录器,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声音材料,使得无法判定《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当时所使用的方音是哪里的。
因为在南北朝时,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民族迁徙,南宋时又是一次。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呈现着一种混同的趋势,往往分不清谁是谁了。古典白话小说中,方言最重的要数《金瓶梅》了。大家基本上都认为,那是以山东方言为主的一种语言系统。但是,现在却竟然有人采用了我们山西应县的方言系统,把用山东方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给解决了,而且成果的确不小。我们能够说《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山东人,或者是应县的人吗!
生活在淮安的人读了《西游记》小说,便发现了其中的淮安方言;但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在读小说的时候也同样会发现,小说的方言属于他们自己的方言系统。如果他们的方言中没有那些词汇,怎么能够读懂小说呢?
章培恒先生发现了《西游记》所使用的是吴语方言系统,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授杨秉祺先生也发现了小说中的方言属于山西晋南或者内蒙西部系统。这是因为他们都从自己的母语中,找到了小说语言的对应。吴玉扌晋、丁晏等人说小说中多用的是淮安方言,正是因为他们也从自己的母语中找到了一种语言的对应。我们是山西晋南人,在读《西游记》的时候,也发现小说采用了我们晋南的方言系统。而且我们也能够用晋南的方言词汇系统,来解决那些淮安方言词汇系统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蔡铁鹰先生《吴承恩确为〈西游记〉作者》(《晋阳学刊》1997,3)或者其他持吴承恩是作者说的人所常引用的几个字,如二十六回的“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解禳作软弱。而晋南人则把东西用得时间长了而变薄软的,都叫做禳,而ráng和软(ruǎn)、弱(rúo)则是一音之转。还有十四回“回头央浼刘伯钦”的“央浼”二字,本来是个书面语,单列“央”字来说明请求的意思。而我们晋南方言同样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央祈”(读作niángj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们却绝对不敢就此来判断,作者就是我们晋南人。所以,用方言系统来判断作者的出生地,实在是不可靠的。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同意徐朔方先生的观点,学问是实实在在的。吴承恩是作者就是作者,不是作者就不要再署为作者,所以我们在新评新校的《西游记》上便署名为“无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