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考补
江庆柏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以下简称《辞
典》)是目前近代文学方面最为完善的工具书之一。《辞典》在收集近代作家
人物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诚如“前言”所说:“本辞典已查考出一批过去
不为人知的作家的真实姓名及生平资料,填补了空白。”但由于近代作家资料
极为分散,又没有完整的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多少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兹就笔
者所知,作“考补”如下。
页50 左锡璇(1829-1891后) 按: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录》卷六云:
“生道光九年己丑,卒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据此,其生年为1829年,与《辞
典》同,卒年为1895年,可补《辞典》之缺。
页67 汉兆(生卒年不详) 按:汉兆《妙香诗草》(道光三年刻本)卷
七《戊寅二月二日余届五十母难口占小偈四则》云:“嘉庆戊寅年五十,乾隆
己丑我初生。”是汉兆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历为1769年;卒年无考。道
光五年(1825),他曾再用妙香室名义刻印诗作《妙香诗草》(版心题《梅花
百咏》),是年57岁。其后事迹不详。
页82 朱绍颐(约1833-1880?) 按:陈作霖《可园文存》卷十一有《朱
子期孝廉传》,述朱绍颐生平事迹甚详。传云:“壬午冬以微疾卒于军,年五
十有一。”壬午为光绪八年(1882),据此推算,其生年在道光十二年(1832)。
又《辞典》谓“生平事迹见《光绪溧阳县志》卷一三”,溧阳为“溧水”
之误。朱绍颐祖籍溧水,与溧阳没有关系。
页167 吴双热(1884-?)按:据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常
熟市志》,吴双热卒于1934年。
页187 何栻(生卒年不详) 按:何栻生卒年不难考订。其《悔余庵诗稿》
卷四《戊午元旦四首》云:“激矢年光四十三,辘轳心事与谁谈。”戊午为咸
丰八年(1858),据此推算,其生年当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他同治三
年(1864)所作《生日》诗自注云:“予与竹庄明年皆五十。”(《悔余庵诗
稿》卷九)这年他49岁,据此推算,生年也正是1816年。诗稿中像这类纪年诗
尚有多首,据之推算,一一吻合。勒方锜为何栻。。《衲苏集》作序云:“嗟
我与君皆丙子。”丙子即嘉庆二十一年,为其生年。此说更为明确。姜亮夫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著录其生年同,卒年作1872(同治十一年)。《中
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著录生卒年均与姜《表》同。此可补《辞典》之缺。
《辞典》著录何栻著作有《悔余庵尺牍》3卷、《余辛集》3卷,亦有误。
《悔余庵尺牍》即《余辛集》。此书封面题签作“悔余庵尺牍”,卷端及版心
均题作“余辛集”,故名称不同,实为同一部书。《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此书,
即作:《余辛集》(一名《悔余庵尺牍》) 3卷。此收何栻与大吏、友朋往来
书信,其中包括他上曾国藩的书信多封。
又何栻还有《悔余庵集事楹联》 2卷,《辞典》未著录。此为何栻于同治
元年(1862)在吉安知府任上罢黜后,滞留于此地时所辑苏轼诗事对偶者而成,
故此书卷端及版心均题作《衲苏集》,卷端并有副题“集东坡先生诗句”。此
书虽不是何栻个人的创作,但反映了他对对偶的注重。《辞典》引《晚晴⺮移
诗汇》评其诗曰:“又喜作工对,韵味反减。”何栻诗作的这个特点(或说是
缺点)是与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的,従《衲苏集》的辑集中可以看到其诗风
源流所自。従这个角度讲,此书也应有所提及。
页198 汪荣棠(1815?-1869?) 按:高鑅泉《锡山历朝书目考》卷十
二汪荣棠小传云:“生道光元年辛巳,卒年五十一。”道光元年公历为1821年,
是汪荣棠生卒年为1821-1871。
页215 张纨英(生卒年不详) 按:太仓王保譿《太原贤媛事略续辑》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张太宜人(纨英)事略》云:“光绪七年卒,年八十
二。” 光绪七年公历为1881年,是张纨英生卒年为1880-1881。
页287 金兰(生卒年不详) 按:金兰《碧螺山馆诗钞》卷七《昌阳砚歌》
云:“丁卯十月十又一,贱子六旬览揆日。”丁卯为同治六年(1867)。这两
句诗的意思是说,同治六年十月十一日,是自己60岁生日。据此推算,其生年
在嘉庆十三年,公历为1808年。《碧螺山馆诗钞》卷末附柳商贤《碧螺山人生
圹志》云:“山人之年甫七十。”此生圹志作于“光绪彊圉赤奋若”,即光绪
丁丑年(三年),公历为1877年。据此推算生年也正为1808年。
《辞典》称其“享年七十二岁左右”,则大致不差。《碧螺山馆诗钞补遗》
有《七十述怀》诗,又有《目病献作》诗云:“七二颓翁病纠纷,日常冥坐避
尘氛。”“补遗”最后一首诗题为《病榻口占示芝儿》,诗云:“行年逾古稀,
考终何足悼。”说明此时已到生命尽头。据此,其卒年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
左右。
《辞典》又引韦光黻《碧螺山馆诗钞序》,称金兰居乎桃花源之地,“得
清旷之气,陶冶性灵,发为歌啸,翛然生尘表,而不为外物所移者”。以此说
明金兰的离世态度及对其诗风的影响。其实在其诗集中,也有大量反映社会现
状之诗,如《水灾纪事》(卷三)叙说了道光二十九年那场大水对社会造成的
巨大破坏,以及官方在赈济中的种种弊政:“黎庶未沾唇,吏胥早吞蚀。以肉
投馁虎,所剩空皮骨。”反映了诗人的巨大愤怒。《地震》(卷三)一诗描述
了咸丰三年那场地震的情形,并探究了地震发生的原因。诗人认为地震之所以
发生,就在于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劫掠日恣肆”,更重要的还有政治的不良,
地方官吏大肆参与财富的掠夺,“凡此守土官,肥遯无不利”。虽然他对地震
发生原因的解释是毫无道理的,但反映了诗人对现实黑暗政治的批评态度。其
写地震时的情景,也极为生动:“有声自西来,硠硠复磕磕。瓿<娄瓦>互击触,
棼橑尽摇曳。妇孺尤惊惶,鸡犬共腾沸。”写得惊心动魄。至于他咸丰同治年
间所写的一些诗,则较多地反映了战争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及下层人民,也包
括自己流离失所的痛苦遭遇,都与现实切切相关。他晚年所写的《禁烟纪事》
一诗(《补遗》),则用纪实的手法,揭露了鸦片烟的危害,并对地方官吏的
禁烟行为表示了由衷的支持,也反映了当时的禁烟运动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凡
此种种都说明了作者金兰对现实的关注,也说明其诗风不能仅用清旷、幽远等
来概括。这是我们阅读《辞典》时应注意的。
页324 俞天愤(生卒年不详) 按: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熟
掌故》(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出版)《人物轶事》“俞天愤”条,称其
1881年4月生,1937年12月死。
又《辞典》称“本名不详”。《常熟掌故》谓其父亲要他留侍左右,不许
离开常熟,因题名承莱,字采生,寓老莱子戏采娱亲之意。其用“天愤”作笔
名,也有来历。据说他曾对包天笑说:“你叫天笑,我认为,现在人世间的一
切,天看了不会笑,只会烦闷(“愤”有烦闷之意)。我就用天愤署名,和你
排行吧。”其后他即以“天愤”为自己作品署名。
页336 姚民哀(生卒年不详) 按:姚民哀生卒年为1894-1938,见1987
年出版《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14辑(常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所刊黄
步青《姚民哀与其作品编年表》。
又《常熟掌故·人物轶事》记姚民哀之死甚详。1937年日军入侵,姚在常
熟沦陷后不久投敌变节,任伪绥靖队徐凤藻部秘书。1938年 9、10月间,姚携
伪绥靖队公文去上海,在常熟境内支塘、白茆间,被琴嘉太昆青松(常熟、嘉
定、太仓、昆山、青浦、松江)六县游击司令熊剑东所属第六梯团第二大队杨
义山部截获,解至司令部军法处。几天后在常熟东张乡法灯庵广场,由熊剑东
主持的白茆军校阵亡学员追悼会上,将姚民哀处决。这段史实各种近代文学史
料集均未提及,故著录于此,以供参考。《辞典》称其“抗日战争期间死于乱
军之中”,说得不甚明确。
又《辞典》谓其本姓朱,名民哀,号兰庵;后入嗣姚家,改姓姚,改名
朕,号民哀。上述《常熟掌故》与此也有不同。谓其原名姚民哀,父亲姚琴
生爱好评弹,也常登台表演。亲戚中有人认为这是辱没家声,姚琴生一气之
下改従舅家朱姓,其子也更名为朱兰庵。朱兰庵有一定文才,能写诗文,又
好写弹词唱篇,在上海结交了不少新闻界人士,其弹词作品为许多刊物录用。
为多得稿费,朱兰庵不免粗制滥造,甚至有窃取《南社丛刊》中的诗词而一
字不易的。此为他人发觉,于是上海各刊物拒登以“朱兰庵”具名的弹词。
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小说,就仍用“姚民哀”原名。
页354 顾荃(1843-?)按:顾荃卒年可考知。顾荃《自怡轩诗存》卷末
有其受业弟子严懋功跋,云:“光绪乙巳,吾师谢世。”即顾荃卒于光绪三十
一年,公历为1905年。该诗集卷末又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子顾宝珏等识语,
称“先君弃养,忽忽已二十有七年矣。”据此推算,卒年也正是1905年。
又《辞典》称其著有《自怡轩诗存》2卷,实际上“诗存”2卷后还有《自
怡轩词存》1卷,本书封面题签即题作《自怡轩诗词存》。
页357钱振锽(1875-1943)按:卒年有误。张惟骧撰、蒋维乔补《清
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本传云:“以甲申八月殁于沪,春秋七十。”甲申为
1944年。《辞典》曾将“小传稿”列为本篇传记资料出处,但不知何以未顾及
于此。
页379 凌泗(1831-?)按:凌泗事迹见其著《莘庐遗诗》卷首沈廷镛撰
《凌磬生府君行述》,云:“府君生道光十二年闰九月二十二日,卒光绪三十
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五。”是其生年公历为1832年,卒年公历为1907
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为1907年2月1日)。
页410 符葆森(生卒年不详) 按:符葆森的生卒年在许多工具书中均未
注明,今在南京图书馆读到符葆森《咸丰三年避寇日记》(1981年扬州古旧书
店抄本),其八月十五日所作七绝志感第六绝云:“四十无成空老大,不堪回
首数年华。”此处“四十”如是实指的话,则其生年当为1814年。又据光绪
《江都县续志》卷二五本传,符葆森得年“五十”,则其卒年为1863年。笔
者当年参加编写《江苏艺文志·扬州卷》(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
因未细考,将其生卒年著录为1805-1854。这是不可能的。因咸丰七年(1857)
符葆森还撰有《国朝正雅集·自序》。
页429 蒋超伯(1817?-1871?)按:蒋超伯生卒年可考。蒋氏《通斋自
记》云:“道光元年辛巳九月十四日生。”是其生于1821年。“自记”记至光
绪元年六月,时年55岁,其子蒋祖{勤心}以此为“绝笔”,是其卒年为1875
年。《通斋自记》逐年记述自己的经历,可当年谱看,是蒋超伯最重要的传记
资料,此当补入本条“传记资料出处”。此书有光绪二年序刻本。又蒋超伯
著作甚多,《辞典》列举了《爽鸠要录》等6种。据《江苏艺文志·扬州卷》
著录,其已刊著作有27种,其中11种收入了《通斋全集》,另有12种未刊手稿
本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1976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以《通斋先生未刻手
稿十二种》为名,影印出版,并收入该公司出版的《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中。
页457 照尘(生卒年不详)按:照尘《药龛集》卷首悲末撰《药龛和尚
传》云:宣统元年腊月初八日照尘晨起作偈曰:“色身原属幻,四大本来空。
悟彻无生理,毗卢性海中。”俄顷拈珠念佛而化去,年八十五。宣统元年腊月
初八日,公历为1910年1月18日。据此,照尘生卒年为1825-1910。
《辞典》在介绍各作家生平事迹时,还介绍了各人的著作情况。这里面
多少也存在一些问题。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作家的重要著作或应该介绍的著作有遗漏;二是有些被介绍的著作
不够具有代表性;三是有些被介绍的著作不是最足本;四是部分书名不够准
确。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加以细考,仅就所知略述一二,有些在上面
考订人物生卒年情况时已作过说明。
一些作家的著述还有重要遗漏,例如孙寰镜条(页126),漏列了他最重
要的一部著作《明遗民录》。该书凡48卷,著录由明入清的“遗民”800多人,
对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有较高参考价值。此书有1912年上
海新中华图书馆铅印本,又有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后又收入谢正
光等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见受到学术界
相当重视。作者在本书署名民史氏,《辞典》未提及,也可补缺。
由于本书是一部文学家的《辞典》,其重点主要在介绍作家生平事迹,各
人的著作不可能介绍得十分详尽,或一无遗漏。唯其如此,所以介绍作家的著
作必须选择最具代表性的。《辞典》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个别地方似可商
榷。如叶昌炽条(页55),称其著有《缘督庐日记抄》16卷。这里应该著录的
是《缘督庐日记》。《缘督庐日记》为叶昌炽原稿,全部约 197万余字,而
《辞典》提到的《缘督庐日记抄》,只是一部摘抄本(由王季烈摘抄),仅约
64万字,只及原稿的三分之一,且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因此无论是
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摘抄本都无法与原稿本相比。叶昌炽的后人及学术界人士,
对这部摘抄本也都不是很满意。因此《辞典》不应著录摘抄本,而应著录原稿
本。原稿本今藏苏州市图书馆,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原稿影印出版,
分装六函48册。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但也说明这些地方确有必要加
以改进。
一个人的著作可能会有多次重印、覆刻,作为一部人物辞典,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将这些著作的版本源流一一罗列出来,但所介绍的应该是最足本。
《辞典》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沈曰富条(页203),《辞典》称其有
《受恒受渐斋集》6卷,实际上沈曰富集的最足本是12卷本。所谓六卷本,只
是咸丰九年所刻的一个本子,而且只是“文集”。同治年间又续刻成诗集6卷,
其中包括他的词作。所以《辞典》介绍其著作,自然应该是这个十二卷本。
《辞典》中列举的个别书名也有误。如钱振FAC2条(页357),称其著
有《星隐庐诗文集》,“庐”字为“楼”字之误。当然著作名称的问题比较复
杂,前人著录对此不太严格。但对一部现代辞典来说,则应力求准确。
《辞典》有些表述还可进一步推敲,以力求准确。如吴昆田条(页173),
称其“与人合著有《清河县志》、《淮安府志》”。此说不妥。方志的编写有
专门的用语,一般称之为“修”与“纂”。“修”标示官修志书的行政领导者,
通常由当地职位最高的朝廷命官出任,如县志的“修”者为知县,府志的“修”
者为知府等。具体执笔编写的人则称为“纂”,有时又有“主纂”、“分纂”
等区别。当然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志(也就是“私志”)也可说是某人“著”的,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而在明清时代,几乎绝无仅有。吴昆田参与“纂”的方志
一共有5部,即光绪《淮安府志》、同治《清河县志再续编》、《光绪丙子清
河县志》、光绪《安东县志》、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此志吴昆田分纂)。
这5部方志今均存世。
个别地方可能由于校对问题,也有一些文字错误,如朱承轼条称其为“江
苏海盐人”(页81),“江苏”为“浙江”之误;俞达条称其有《青楼梦》四
十六回(页326),应是六十四回。问题虽不大,也影响到本书的质量。
以上这些问题如能注意避免,则本辞典可更具权威性。
此外,一些数字的用法似乎也不太符合一般人的习惯。《辞典》在使用数
字时,除去了“十”、“百”等表示位数的词,而直接用具体数目,如不说一
百三十一,而说成一三一。这种方法用来表示序数是可以的,但用来表示基数,
则不妥。如陆增祥条(页236-237),《辞典》称其生平事迹见《续碑传集》
卷三八,这是可以的。但说他著有《金石补正》一三○卷、《篆墨述诂》二四
卷等,则多少使人感到别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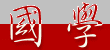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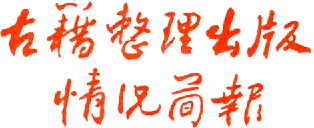 组办
组办 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