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忆白寿彝、赵守俨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
崔文印
中华书局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白寿彝先生是组长,赵守俨先生是
副组长。他们无论在工作例会,还是在私下谈话里,都对古籍整理谈过好多
精采见解,今杂忆如下:
大约1972年末或1973年初,在评审《金史》前几卷校勘记的样稿会上,
白先生说了大意这样的话:搞古籍整理,不仅要对今人负责,也要对古人、
后人负责。明人刻书而古书亡,那就对不起古人,也为后人所指责,我们不
做那样的事。
他针对校勘记中“某字原无,今加”之类的写法说,我们要用校勘规范
术语,改成“某字原脱,今补”。他说,“无”是本来没有其字,是我们
“加”上去的,这不符合校勘“求真”的原则。用“脱”就不一样,这意味
着这个字本来有,只是在刊刻或流传过程中“脱”落了,因而我们现在将其
再行“补”上,这就符合校勘的基本原则。他针对删补较多字的校勘记说:
删多少字或补多少字,一定要标明従某字至某字共多少字,不要使后人看不
清楚或造成误解。最后,他特别指出,无论删还是补,都必须把理由和根据
写清楚,没有充分的根据,是不能对古书做任何手脚的。
在兴华胡同寓所,白先生谈到古籍整理与出版时说,古籍出版应该影印
与整理点校双管齐下。他特别强调影印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出版方式,可以将
古籍的面貌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这对善本书的流传和使用尤其重要。他还
特别指出,某些几十年前的学报,如《燕京学报》和《辅仁学志》,中共早
期的刊物等,都应该通过影印,发挥它们的价值。他说,古籍固然需要整理,
但这比较花费时日,不可一蹴而就。比如咱们点校“二十四史”,集中了这
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足可说明这需要下一番硬功夫,要是对所有古籍
都这么整理下去,就不可想象了,因此,一边整理一边影印,不仅必要,也
是切实可行的。
白先生说,通家校书,自古如此。所谓通家,就是专门家,他必须具备
某一方面的知识,才能胜任校理某一方面的古籍。对出版社来说,必须有一
个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这样才能保障古籍整理高质量的出版。白先生十分
赞扬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置,认为这涉及到古籍整理队伍的建设问题,
十分重要,也十分有意义。
守俨同志作为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负责人,对古籍的校勘问题
十分重视。有一次谈到“择善而従”。他说,采用底本进行校勘,不能“择
善而従”,而只能最大限度地遵従底本,在必不得已,也就是如不是在文义
不通的情况下,不能改动底本。他申述,底本就是蓝本,就是该书的基本面
貌。不能因为校勘而改变了底本的固有特色,这就是为什么选用底本进行古
籍校勘不能“择善而従”的原因。
但另外一种类型的校勘则与此恰恰相反,它的文字不主一本,而是用多
种本子拼起来的,因而,它的校勘原则正好是在诸本之间“择善而従”。
《隋书》即采用了九个本子相拼,而且,版本之间的校勘一般不出校勘记,
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这种校勘,也用一本子作为工作用书,但这个本子不
能叫底本,就暂时叫“工作本”吧!他接着又说,“工作本”这个名称不好,
因为“底本”也可以说是“工作本”,究竟用什么名称好,以后再说吧,暂
时先叫“工作本”。同时,他还指出了这种校勘的缺点,因为版本校一般不
出校勘记,因而不能知道诸本间的异同,如果将版本间的异同也写入校勘记,
就更为理想了。
以上追忆,不一定都是原话,但其意思还是大体准确的,谨供参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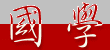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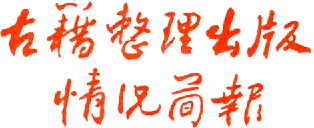 组办
组办 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